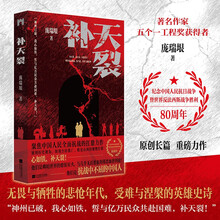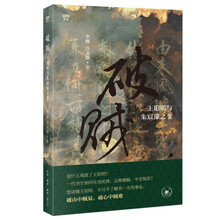童年的记忆<br> 童年如果是以1至12岁为记,正好是我父母双亡时期,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这个时期的记忆,是无法从心灵中消失的。<br> 我生于1947年,成长在湖北一个非常偏远的农村,家庭人口众多,排行老六,上面有夭折一兄,下面又夭折一弟。所以,我刚断奶,就又重新吸食母乳。那个时候不懂得是弟弟夭折,我才多吃了一段时间原本属于他的母乳。这是后来大一点,母亲告诉我的。虽然喝母乳较长,但后来的体质并不好,从小体弱病多,主要是肠胃病,俗称“气痛”——小时候经常食不果腹。<br> 我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父亲在我6岁时卧床不起,是有病无医的情况下走的,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都不算大病。而母亲是在两姐三兄各自成家立业以后,因病而故,当时叫做“血进病”,丢下了我。从此我的学业也就停了,13岁开始独立生活,打鱼摸虾,度过漫漫长夜。<br> 儿时最多的梦还是打鱼摸虾,我的降生地就在水边——梁子湖。人们知道较多的是洪湖,而长江岸边的梁子湖,许多人并不知晓。梁子湖畔青山秀水,有良好的湿地和生态环境。在湖西南岸一个小村子,我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br> 那个时候,我的家乡是没有任何现代交通的,直到60年代,才有了柴油机船,早先两天一次来回,经过梁子岛和九十里的长港水路,从早上六时开船,下午四时才能到达繁华的鄂城县,樊口就是到达的最后一个码头。儿时骑在牛背上远望湖面上白帆点点,那是渔民们的渔船——一家人捕捞和生活在这只小船上,船的尾部还养着几只鸭子。<br> 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运输船,把县城里的坛坛罐罐、油盐酱醋运到这里,供给附近的村民们采购。运输船上有丈余高的桅杆,是用白布做成的帆,遇上顺风把帆扯起,老板们在船的后端跷起二郎腿,看起来倒还自在。一旦有了风暴,他们可就倒霉了,翻船的事常有发生。那个年代没有天气预报,全靠人们早上起来看天色决定这一天是否出行,何时出行。<br> 船所经过的宽阔湖面,清清的湖水一眼可以看到水底各种青绿色的水草。这水下成片的水草吸收了水里的各种养分,养育着梁子湖水中的150多种淡水鱼,也净化着这片水域。鱼类中最有名的就是武昌鱼,名满大江南北。“武昌鱼”得名于毛泽东的诗:“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另有一种水草,当地叫鸭舌草,大片大片的;冬天北风刮起,能将这草拖出,浮出水上,随风飘浮,一层一层的,正好供远方来此的候鸟食用;数以万计的候鸟撒下的粪便,又是第二年春天这些杂草的最好肥料。(完美的自然生物链可惜现在都破坏了!)<br> 我家的四周生长着各种水生植物,水中有菱角、莲藕、篙秧、鸡老苞,还有水边生长着的数不清的水草,像荸荠草、水蜡烛、苍蒲,现在几乎都灭绝了。这些水草,对于生长在这片湿地上的鱼虾来说,既是藏身之地,又是繁殖后代的温床。湖水与湿地相连,山水相映,一年四季鸟语花香。<br> 在我步入社会,出游在外的数十年里,每当听到“洪湖水啊浪打浪”的歌声,尤其“早上出门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的歌词时,就会想起我儿时的生活情景。如今在我梦中出现最多的还是儿时捉鱼的那种情景——魂牵梦萦我几十年的就是家乡的水,家乡的鱼,家乡的一切,以及我孩童时的憧憬。<br> 1954年,那场特大的洪水,把我们赶到山顶,只能搭上一个草棚寄宿。洪水同时也把水下的各种鱼推到山林边。抬头望去,四周除了水就只能见到几棵被洪水包围了的特大特大的枫树,而树权上挂着太多太多的鸟窝。在那场史无前侧的洪水期间,水占领了我们的生活区域和家园。半年之后,田里、池塘里、水坑里,处处都是鱼虾。已经快6岁的我,每天光着屁.股去捉鱼,经常看到比我大的鱼,也比我重。<br> 大人在山上砍柴,一堆一堆地晒干,而一堆一堆的柴火堆下面,则是一堆一堆的乌龟。如果将那时的乌龟捉去如今的市场上卖,估计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万元户。但是那个时候不仅没有人卖,许多人也不吃龟。父亲有时拿棒槌从侧面打破龟壳,用顶罐(也是铁锅)把水烧开,再把火钳架在顶罐上,让龟慢慢爬过去,由于蒸气的作用,龟就会自动掉进顶罐,经几分钟煮熟以后,捞起来加工一下,好香好香!<br> 那时我捉龟只是为了玩,有时候放在地窖里(地窖是用于存放红薯种的),放上几十甚至几百只乌龟,没有几天就又都跑了。爬树掏鸟窝、放牛、养狗、放鸭子,都是我那时的“正经事”。如今我最爱看的电视还是“动物世界”。同动物打交道最多的人,最懂得生活,最有能力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找到自我、生存和发展下去。人类、动物、大自然三者的和谐才有当今的世界。<br> 在父母的双翼保护下,兄长们是不敢打我的。我唯一的一次挨揍也是在发洪水期间。<br> 洪水来临之前,天天听到的是远处大人用硬纸做成喇叭发出的呼喊声:各家各户注意,今天水位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大家要……<br> 我和一群小兔崽子三四个,没有一个穿着衣服的,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眼看洪水暴涨:由大门口下、房子脚下,一直上升、上升,土巴瓦房摇摇欲坠;刚升到两三米,也就是房子的一半时,一声巨响,接着就是一柱带黄色的浓烟腾空而起高达十几米。我们高兴得直蹦,拍巴掌,闹个不停。大人走到跟前,几个巴掌把屁股拍红,还没有等我来得及反应到痛不痛的时候,祖辈用双手垒起来的土屋,养育了几代人的老屋突然不见了——一间一间的房子都被洪水吞没。<br> 这次挨揍以后,才让我意识到:没有家了。再也回不到我从前降生的那个家了,除了我眼前的一片汪洋大海般的情景以外,就是满面泪水的大人——众多的大人,抱成一团哭嚎……半年多的时间,出行困难,亲友们很少有往来,母亲挂念着出门远嫁的两个女儿,时常落泪。<br> 一场浩劫以后,我们回到原来的村落,剩下的是一堆泥土和瓦片。在各自的屋基上,人们开始重建家园。我们帮助大人收捡好被淹过的一切。<br> 洪水走了,父亲也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连他的容颜现在都无法记忆,直到如今,我仅知道他安葬的地方。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