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虹:心有余悸,有过那个年代的经历。<br> 沈昌文:现在我退休了,当然我可以不那么想了,可是事情要有成效,必须要有一种坚决的主张,要有独断的主张,这是我的办法。所以讲起来我这个人是比较专制,比较独裁,可是我喜欢采取民主的形式,喜欢采取傻帽的形式。最好是在傻兮兮的帽子之下做一个独裁者,我觉得是领导人,像我们编一个小杂志的领导人最需要的气质。我讲的这些都是要挨骂的,我也只能挨骂了,对不起。(笑)<br> 晓虹:我觉得你说的里边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人生哲理,因为一方面您是民主了,另一方面您也集中了,但是另一方面您也把事情办成了,就是这样子。讲和听都是一种艺术,“听的懂”不容易沈昌文:我的领导比如说陈原先生,我有一篇文章不知道你看了没有,讲陈原的几句外国话,我文章没有写透,实际上陈原的每一句外国话背后都有深刻的用意。陈原碰到了不好解决的事情,难办的事情,他就跟我一句外国话。<br> 晓虹:那时候您都能够听得懂吗?<br> 沈昌文:那当然了,不但语言听得懂,要把背后的意思听得懂,那就更难了。<br> 晓虹:您书里说是有好多不可言说的事情。<br> 沈昌文:对,尤其是他那样的高级领导,他要说一句话,那就不好说得很透彻。<br> 晓虹:那样的话会不会很累,老是要去想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br> 沈昌文:本来工作就应该这样做。<br> 晓虹:这是一种艺术。<br> 沈昌文:这是一种艺术,所以他的外国话水平比我更高了,我就到了能听懂他的外国话——也许一辈子他讲的外国话我没听懂的还多着呢。<br> 晓虹:实际上我们常常说,除了(学校)这种通常意义上的这种学习以外,实际上社会也是一所学校。我看到您的自传里说,您在陈原还有陈翰伯这两位老先生的旗下,觉得自己好像上了一个研究生班一样。我在看您的书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一个感觉,比如说您是从小时候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到了您在银楼里当学徒的时候,也是坚持学习。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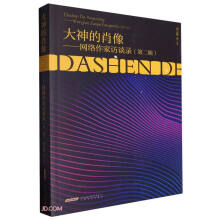


——江平(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我今天能够做这些事情,放在过去的环境里边,不但不能做,连想都不能想,一想就是犯罪。现在已经可以做了。这样我觉得就很高兴,用一句蹩脚的英文讲“I am so happy”。
——沈昌文(《读书》前主编)
《绞刑架下》,这本书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狱中写给他的妻子古丝坦的。作者伏契克说:“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在我一生中,一直到晚年,我仍然可以背诵其中使我热泪盈眶的许多片段。
——汤一介(哲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
科学事物,必须不断研究,认真实验,得寸进尺地深入、扩展,通过韧性的战斗,才可能获取光辉的成就。
——陈佳洱(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
我就感觉到人的一生总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要完成自己的信念去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最有意义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我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把这件工作完成好,做完。
——草婴(著名翻译家)
当一个医生面对病人时,实际上他已经面对了整个社会。
——张丽珠(北京大学妇产科专家,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