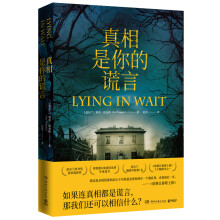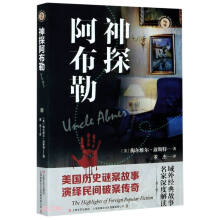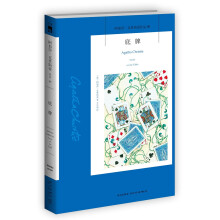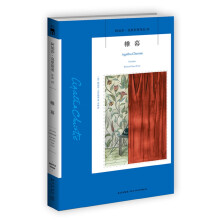姜:您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史的叙述,不应只讲北大,不讲清华,两者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都在为中国新文化奠定基石。应当把与“五四”主潮(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之外的具有不同理念的清华大学学者的人文论述(包括王国维、梁启超、吴宓等)纳入新文化的范畴。能否具体谈谈他们共同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多元文化景观?
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北大,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都属北大,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清华总是被视为新文化的对立面,却不公乎,错觉的原因是因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三个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均是保守派。尤其是吴宓,他和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胡先辅等先生创办的《学衡》被视为《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反动。其实,吴宓编辑《学衡》杂志期间(1921-1924)身在南京东南大学。直到1925年初,他才被聘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不过,他是1917年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派往美国学习的,因此被视为清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也理所当然。在吴宓的主持下,1925年梁启超被邀担任研究院导师(于1928年夏季辞去职务)。同年,王国维也受聘于研究院,并携全家迁居于清华园,两年后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嘱家人把他“行葬于清华园茔地”。
1988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人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20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最”字。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