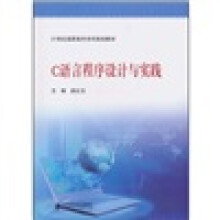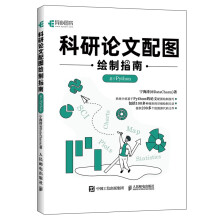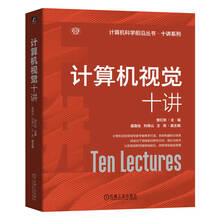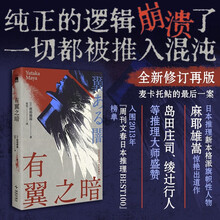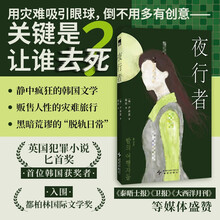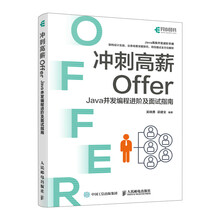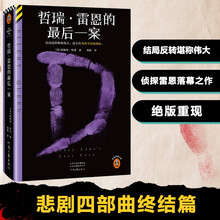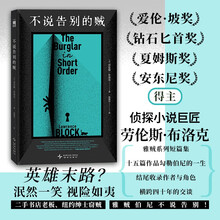在春秋战国之交,我国黄、淮、江、汉流域已基本结束了各部族错居杂处的状态,成为一个单一的华夏民族的聚居地。在这块地域内,原来与周族错居杂处的“蛮、夷、戎、狄”各族,大部分与周族共同融汇于华夏民族中,小部分则迁往了边远地区。这种现实反映到人们观念中,是春秋末年的文献中开始出现“四裔”的称呼。战国以后,人们普遍认为居住在周边地区的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蛮夷”。只有华夏居住的“中国”(中原)才是文明礼仪之邦。“中国”成了华夏的同义语。用恩格斯的话说,中原地区已实现了“各个部落领土融合成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这个时期还存在着若干个诸侯国之间的割据,但这种割据是封建性的政治割据,而不是不同部族或部落的对立。各国人口流动,商旅云游四方,士大夫求仕于不同国度,反映了各诸侯国之间并无种族隔阂。换句话说,各诸侯国的所有土地,都是华夏民族活动和居住的共同地域。
其次,在各华夏国家内部,由于阶级分化日益深刻,彼此混居的各族氏的界线也告消泯。试看西周初年的铜器,往往继承商代作风,铭有标志各族氏的“族徽”,到了西周中后期,铜器上的“族徽”便开始减少。春秋时竞至绝迹。与此相应,无论在铜器铭文或是在文献中,都再找不到像商周时期那样把整族的人们不分贵贱地视作一个整体,动辄“令某某族”,“赐某某族”的做法。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曾论及春秋战国两个不同时代的根本区别,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春秋宗法氏族之称于战国乌有。可见这种现象早已为学者所关注。
由于氏族血缘联系不复存在,国家开始对其臣民按地域行政区划实行统一治理。春秋末期,晋、楚、秦、齐、吴都实行县制,或者郡制。虽然春秋时期的县还往往作为封邑对待,楚县直属国君,而县尹(或称县公)的任命也还脱离不了世卿制的影响,但随着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封邑制向食邑制的转化和世卿世禄制向官僚制的转化,县作为国家地方行政管理单位的性质越来越明显。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