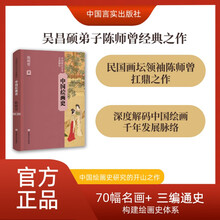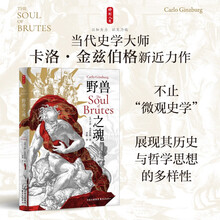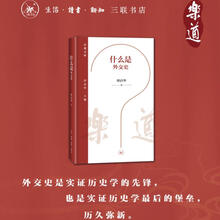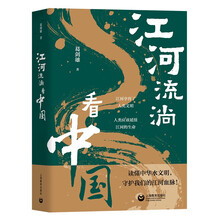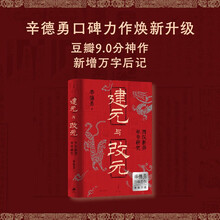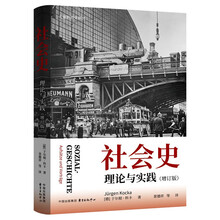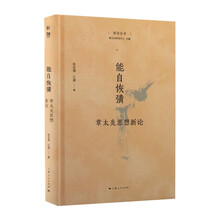职事官体系与使职体系交叉,带职事官而理差遣事任,出则任差遣,归则复本任,这种办法的普遍行用,很容易造成官员管理中的混乱与不便。诸如带本官者与其“本曹”的关系,以及是否应按“在朝叙职、人省叙官”的原则排列次第等敏感问题,自唐至宋争论不休①。
中晚唐时期,既是以种种权宜措置破坏原有官制的过程,又是尝试对设官分职之制进行整理,力求建立能够相对稳定运转的官僚机制的过程。
这一阶段中,职事官队伍已经改变了性质,而差遣体制尚未发育成熟。反映在任官制度中,实际上出现了“双轨制”的局面:一方面,“官”有员额有品秩,却不一定有事权;另一方面,拥有事权的差遣“职”,却由于本属权宜设置,任命不经有司,既无品秩又无员额。
这种状况引起了士大夫们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当时整理任官制度的努力,归结起来,是希望恢复(而非另建一套)以职事官为中心,把官称、员阙、品秩、事任联系在一起的设官分职方式。
早在武后时期,李峤为吏部尚书,许员外官厘务,“至与正官争事相殴”,于是用“停员外官厘务”②的办法,把他们与正员官加以区别,维护了职事官的正常工作秩序。中宗、韦后时期过后,宋璟、姚元之主持铨选,一改逆用数年员阙以迁就选人的做法,以“量阙留人”为方针,尽力保证治事队伍的效能。直到德宗时期,陆贽提出注拟时“计阙集人”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了铨选中以职事官“阙”为本位的政策与思路。面对官员总额剧增陡涨的形势,朝廷中的有识之士逐渐把限制冗滥的着眼点转移到直接选授任职的“阙”额方面。于是,不仅有正员官与员外官的区分,又有了“厘务”与不厘务、“视职”与不视职、“占阙”与不占阙的类别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