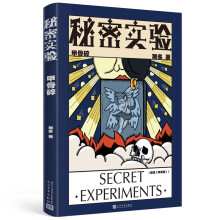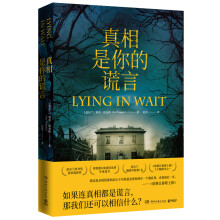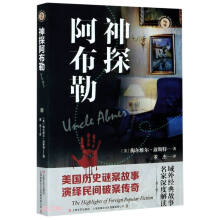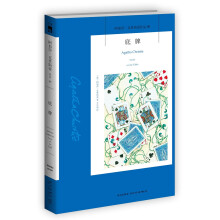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需要它的文化起作用。近代100多年来,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来侵犯东方国家,整个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方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家先后都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谋求自主和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纷纷发展起来,得到了自主,80年代后开始振兴。随着经济的振兴,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之前,这些亚洲国家因为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种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倾向。可是当政治和经济恢复以后,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就开始有一种自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政治与这些东方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的不同。怎么调整、处理这些不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些国家都想向西方学习,甚至想甩掉自己的传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总是和现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辩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强烈,但我们传统的许多东西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父债子还”这个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而且根深蒂固。如果不认同,他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西方文化后,整个社会氛围中大家还认同这一点?这源于一个基本的认同,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个个体,无论是他的肉体还是灵魂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每个个体都跟上帝发生关系。虽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赋予他父母的一种责任,他和父母是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儿子跟父母都是兄弟姐妹,上帝给他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他有义务要把孩子养大成人。每个个体生命没有一个绝对的责任,而是大家共同对上帝负责,上帝为大家,人人为上帝,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贡献给上帝才有意义。所以,生时增加上帝的荣誉,死后灵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辈子都做有损于上帝荣誉的事,死后灵魂就要下地狱。因此,西方文化中个人的价值是被突出强调的,个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
另一种生命观以印度文化为代表。印度文化也强调人的生命是个体的,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轮回的。这种轮回都是由神决定的,像婆罗门教讲是由梵天决定的。后来,佛教兴起后就批判婆罗门教由梵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轮回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行为,即佛教术语中的“业”,包括身、口、意三业。身,就是身体,也可以说是行动;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论;意,就是思想。所以一个生命的生成以及这个生命的轮回都是由身、口、意三业决定的。如果他的“业”没有消掉的话,他的生命就永远轮回。这样的生命观也是个体自身的,和其他人无关的,只不过是他自己的“业”没有消掉,所以借助他的父母生下来,而跟他的父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生命观中,生命都是个体,和其他个体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其他个体的问题要由其他个体自己解决,跟“我”这个个体没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每个个体只是族类生命锁链中间的一环。中国人讲生命的延续,但不是个体生命的延续,而是族类生命的延续。他死了,他的生命由子女延续。所以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因为“无后”就不能延续生命了。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断子绝孙”,断子绝孙后他的生命就彻底结束了。因此在中国,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而且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父母遗留给他的,他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遗留。在这种生命观念中,“父债子还”就顺理成章了。
有很多传统观念是深入我们血液中的,永远去掉不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会落实到文化上,而不仅仅是落实在经济上。所以文化的继承发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就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常讲爱国主义,要爱国,就要认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历史又落实在文化上,因为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认同历史也就是认同这个文化传统。龚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感情呢?从这个方面讲,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事关我们国家、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且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近几年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在现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也是这样。中华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百家,这个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相互交流、影响。通过这样的交流,到了汉初一些学派开始壮大了,也有一些开始衰落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介绍了当时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学派的思想,百家变成了六家。这六家经过汉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后又有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形成了儒、道两大家。这两家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靠什么?就是靠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一种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发展。后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加入,对于当时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儒、道两家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中国民间的一些习俗中。一种思想只有落实到生活习俗中去,它的生命力才是强大的,否则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和认识。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为中国原有的精神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强大的,中国弱就弱在物质文化方面,所以要赶上西方只要在物质文明上积极学习和发展就可以了,这就是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建立起了当时非常强大的北洋水师,可是在一场甲午战争中就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开始考虑体制、机制的问题,考虑制度文明的问题。儒家的文明不行,就要批判,就要改,所以要进行制度改革。西方提供了我们两种榜样,一种就是像英国、荷兰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把国王架空,实权放到议会当中,这就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可是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在随后的第二个阶段中,孙中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但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因为虽然把皇帝拉下了马,但是旧军阀势力又非常强大。于是人们开始思考精神文明层面的因素。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改造精神文明,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些实际上还是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对于一般世俗生活中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冲击多少。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铲除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很多生活习俗消失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在基本的家庭生活中也把我们的传统割断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基本的家庭伦常观念不是很清楚,有的根本不认同。
二
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这还“直在其中”?这不符合法律。所以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合情合理合法,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合理合法可以接受,但合情不能接受,认为法律是没有情的。法是不是就不容情呢?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韩国,想了解一下儒家文化在当下韩国社会中还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对包庇罪怎么处理有这样的规定:如果隐匿者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根据他的罪状,要判10年;但如果同样的情节发生在和他有血缘的直系亲属之间就可以减刑。这在我们看来有点儿荒唐。但我仔细看他们伤害罪里还有一条,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没有亲族的血缘关系的,根据他伤害的轻重判5年;但如果是直系亲属之间的关系,就得判10年。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法律的意图:重视亲情。我们都知道韩国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极深,所以我看到这两条后马上就想到孔子这句话。
我们人间之情大致归纳起来也就是三类:一是亲情,二是友情,三是爱情。这三类“情”中最不稳固的就是爱情。亲情、友情应该是永恒的,爱情却是变化的。两个人有爱情,到一定程度后结合了,这个爱情已经转变成亲情了,亲情就不能像爱情那么随便了:我们好就在一起,不好就分手。他要考虑相互之间的责任,这就是亲情的要求,就不能够还停留在爱情上了。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礼是婚礼。礼,始于冠、本于婚,但现在的婚礼可以说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吃吃喝喝,吵吵闹闹,顺便恶搞一下就完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规范一下婚礼,要让两个人通过婚礼受到一种教育,认识到责任发生变化了,双方都要为对方负责;婚前如果讲孝道的话,他只要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了,结婚以后还要为对方的父母尽孝道。如果有了子女,以后他还要对子女负责任。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婚礼上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呢?就是要感恩,让他有这种感恩的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