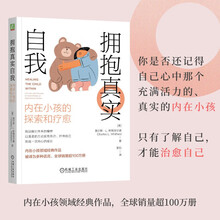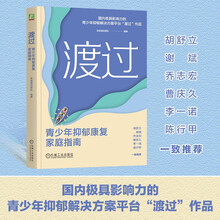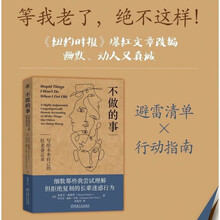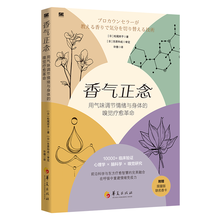关于卓尔这个人,有两件事你得先知道。
首先,他是一个聪明绝顶,身高不满5英尺的海地人,拥有十分宽阔的肩膀和健壮的体格。他相貌堂堂,咖啡色的皮肤和欧洲人的面孔显示他是个混血儿。卓尔说起话来沉稳迷人,有着让人放松的加勒比海式轻快语调。
其次是,他毁了我的人生。
1 如果有人要你收下你不想要的礼物
3月下旬的某一天,我和卓尔初次见面。那天天气晴朗,温度大约接近华氏60° 。在大部分的国家里,这样的温度也许算冷了,但是对于刚度过漫长寒冬的波士顿居民来说,60°已经是宜人的喘息。
日光节约时间最近刚开始,我决定下午散步到波士顿大众花园,藉此庆祝春天的到来。走到鸭子池转弯时,我发现有一个人只身从博尔斯顿街走来。他虽然个子很矮,但是走起路来却昂首阔步。他那步伐像是用滑的而不是用走的,引起我的注目。
当他走近时,我发现他不只是矮,他根本就是个矮冬瓜。我看不出他的年纪,他的步伐则带着自信的节奏。
我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他的人。他走过坐在公园长凳的两个年轻人身边,其中一个对他品头论足一番,引得另一个嗤嗤讪笑。矮子对两人视若无睹,继续前进。
他不理不睬的态度激怒了那两个年轻人,于是他们迅速跳上前去,挡住了矮子的去路。双方开始交谈,起初还算平和,后来就起了冲突,并渐渐变得白热化。我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但两个年轻人的声音越大,矮子就越显得沉着。
在得不到任何响应的情况下,挑衅的两人越来越激动,比手画脚地大声咆哮,但矮子只是站在原地,摇头说不。
周围似乎没有其它人注意到这件事。我开始担心起矮子的安危,于是想趋前打圆场。但是,我多虑了。
很快地,两个年轻人觉得自讨没趣。他们因为没能把事闹大,感到很沮丧,摸摸鼻子自行让开了。泄气的闹事者闪到一边后,矮子继续往前走。
我被这一幕给震慑住了。我得和这个人谈一谈,看看他是如何轻易地就把找麻烦的人给打发走。我拦住他,边走边聊了起来。
“请问,”我说,“刚才我看到那两个人在骚扰你。你是怎么保持沉稳的?”
他笑了笑,用加勒比海式的轻快语调说:“我想,那是我的天性。”
我继续问:“你摇头的时候,都和他们说了些什么?”
“不了,谢谢你们。”
“‘不了,谢谢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婉拒了他们的礼物。”他说。
“我不懂。”
他停下脚步,耐心向我解释:“如果有人要给你一个礼物,而你不想收下它,那么拥有那个礼物的人是谁?”
“我想应该是原来那个送礼的人。”
“完全正确!这两个男孩试图给我他们的礼物,那个礼物就是负面的‘气’。”
“气?”我重复道。
“正是‘气’,那是他们的生命动力,他们的业,他们的能量。没有什么东西比负面能量更毒了。一旦你接收了负面能量,它会恶化、蔓延并污染你整个生命。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将这种毒素转移到其它人身上。这些男孩的身上充斥着负面能量,这种能量就像嗜血的病毒一样,将他们缓缓吞噬。他们拚了命地想要把他们的‘气’转移给我,但是当他们明白我一点都不想响应他们,不想分担他们的愤怒,不想接受他们的礼物,他们只好离开。”
说完,他不再作声。我不太懂他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说完了。
“呃,不管怎么说,那一幕真是太了不起了。”我边说边伸出手‘“我叫约翰,约翰?布鲁斯特。”
他的手虽小,但是握手时很有力,劲道出乎我意料。在我转身离去之前,他点点头说:“我叫卓尔。”
7 面对它,但别耽溺其中
“嗨,很高兴又见到你。”我轻拍他的背,发现他比看起来更结实。他回了我一个微笑。
“杰克……杰克,你过来一下。”我喊着(经过了这些年,杰克之屋的酒保都被人习惯性地称作杰克),杰克走过来,放了一个杯垫。“杰克,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个人。这位就是我和你说过的,几个星期前在波士顿大众花园被骚扰的人。”
杰克看起来还没搞清楚。
“卓尔,”我解释,“这位就是卓尔。”
“哦,你好。”杰克说,“很高兴认识你,索尔,我能给你上些什么吗?”
“索尔是挪威的雷神。事实上,我的名字是卓尔。”
“卓尔?”
“卓尔。”
“那好吧,卓尔,我能给你上些什么吗?”
卓尔想了一阵。
“酿者之徽波本威士忌,纯的。”
酒送了上来,在小啜一口之前,卓尔朝我举杯致意。
“你在这附近工作吗?”我问。
“不是。”他说。
“你住这附近?”
“不算是。”
“那好吧,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为了纯的酿者之徽波本威士忌。”他面带微笑重申了一次。
一阵沉默后,他用比我先前更严肃的口气问:“你又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拿着饮料,指着损坏的时钟,时间停在5点10分。
“每当它停在5点钟的地方,我就会出现在这里。”
“每天都来吗?不论晴雨,不论心情好坏,不论春夏秋冬?”
“这是属于我的时间。”我试着让口气听起来不那么有防卫性,“是我放风的时间。”
“是放风,还是逃避?”
听了他的话,我觉得不太自在,转过身打算把账单付了,但脑海里却清楚记得他刚才说的那句话。
“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问。
“哪一句?”
“你说面对它,但别耽溺其中。”
“你有听到?”他诧异地问。
“你就坐在我隔壁,我当然有听见。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面对它,但别耽溺其中。”
“我知道你说了什么,我问的是它的意思。”
“意思是,要去面对你的问题,但别耽溺在问题里。一个人如果专注在生命的消极面上,他的灵魂将会枯竭。你应该要找出负面能量的根源,然后将它逐出你的生命。”
“要是我把人生里所有让人意志消沉的东西都赶跑了,我的人生可能会变得很空虚。”我半开玩笑地说。
“正好相反,你最后会变得很充实。”
“我的人生已经够充实了。事实上,我的人生好得不得了。”我也许说得太过头了,“我对我的人生毫无怨言。”
“一分钟前你似乎还在抱怨呢。”他边说边朝贝丝刚空出来的高脚椅示意。
“哦,那只是醉话。”
“你喝醉了?”卓尔问。
我故意忽略他的问题不答。
“人们称工作为‘工作’是有理由的,要是它很有趣,那就会被称为‘度假’了。再说,工作是我一天之中最棒的部分。”
“这是你之所以在这里的原因吗?”他边问边看着我的结婚戒指,“好让你不用回家面对老婆?”
“我告诉过你了,我会在这里是因为我想从工作里解放一下。我喜欢回家和我太太在一起。”
“我觉得你实在太爱狡辩了!”卓尔微笑地说。
我忘了付账单的事,又点了一杯来喝。酒送上后,我继续说下去,但那些话听起来比较像是说给我自己听,而不是给别人听的。
“我并没有说人生一切完美无缺。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我太太,也许现在感情是有点褪色了。但我们结婚已经超过30年了,我们的爱很成熟。”
“怎么说?”
我想了一下,脑海里回到我们在波士顿大学的时光。
“那是脑袋一片空白、心跳加速、全然迷恋的爱情,之后蜕变为更成熟持久的婚姻。我们转变成能够面对孩子、承诺和压力的人。热恋成长为包容是一件很健康的事。”
“也许很健康,但对我来说听起来很无聊。”
“无聊?”我大笑说,“相信我,我的婚姻一点都不无聊。”
卓尔作势要我跟他一样把身体斜靠过来。“你爱你老婆吗?”他问。
“我当然爱我老婆,而且她也爱我,我只是不确定她有多爱我。安逸的依赖似乎取代了激情,就好像布鲁斯?史普林斯汀唱的那样:‘所有看似重要的事,都消逝在空气中。我像是什么都不记得,而玛丽则像是什么都不在乎。’”
“你好像失去了连结。”
我啪地一声拍了一下吧台。
“正是如此!我就是在找这个字眼。连结、连结、连结!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完美连结的时光。她是阴,我是阳,而如今我们只是被放在一起而已。”
我们双双陷入一阵沉默,然后卓尔说话了。
“如果我说我能把她交还给你,你觉得如何?”
他的语调让人胆颤,而他的话让我卸下心防。我依旧保持沉默,纳闷着究竟让自己陷入什么样的处境。
“交还给你的意思不是指她的肉身,而是指她的心灵。如果我能够让你们的关系和婚姻回复到那段所谓脑袋一片空白的过去里,你觉得呢?”
我继续保持缄默。
“你放心。”他再三保证地说,“这不是什么魔鬼的交易,我并不求回报。”
再一次地,我像是在和自己而不是和别人说话,我说道:“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我俩回到过去。”
“这其实很简单的。”卓尔得意地说,“你只需要认出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就可以了。每一件事都是某件事的果。想拥有你所没有的,你必须去做你没有做过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