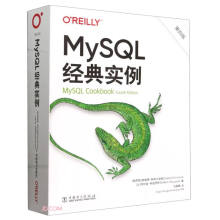这三种形式上相去很远的文体放在同一本专著中,给以平等的学术地位,有一个很小的学术心愿:通过这种体例结构消解“作者中心”的成见。国内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民族志写作,一直存在着一个争论:照描(即忠实客观的记录)与理论思考谁更有价值。坚持照描观点的学者认为,许多研究者理论水平不高,在文化呈现过程中,对民族文化肆意剪裁,常常歪曲了文化真相(即远离了文化本相),因此民族志最好是照描的著作。坚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照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没有经过理论加工,因此没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国内学术实践中,基本上是第二种学术观点占上风。因此,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些默契,就是学者的理论专著的价值高于照描的田野调查报告。(举例说,在国内的学术评价中,理论专著可以作为评职称的重要依据,但是那些照描的民族文化志,则只能作为参考依据了。)为什么人们偏爱理论思考的著作呢?我们猜想,一是理论思考的专著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二是人们潜在地确立了“作者中心”的成见。何谓“作者中心”成见?就是潜意识地认为,作者的理论加工在民族文化呈现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因而,把作者的理论活动看成是整个民族文化呈现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最有价值的环节。
写作者在文化呈现活动中,确信的“作者中心”成见并不能抵消他们对原始素材重要性的看法,所以,相当多的作者同时在专著中以附录的形式,收录大量比较原始的典籍文本,并为自己的这样处理想出了一个很实在的理由,叫做供读者以及其他研究者“参考”。有时候也可以将其单独编辑成书出版,但那被看成是史料,也仅仅是研究的“参考”。
许多时候,民族学家对待民族文化的持有者与表演者的自述(或者说是对话)时,也存在类似的矛盾心态。大家都认为这些自述(对话)非常重要,但是,到底重要到何种程度?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