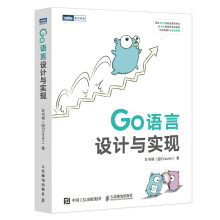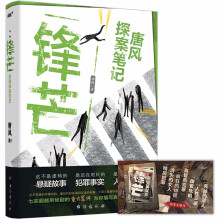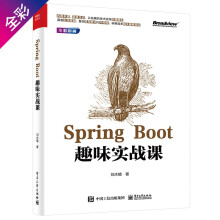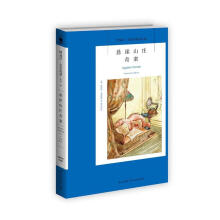郭影秋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调新市委
1965年9月12日起,我带领人民大学数百名师生到北京郊区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6年5月上旬,中央组织部的赵汉副部长突然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做文教工作。”面对突如其来的调动,我经过认真思考后,非常诚恳地向赵汉表示:请转达中央有关领导,能否准予免掉。但是不久,我的请求未被接受,中央明确通知一定要调。
我清楚地记得,5月18日,吴老(吴玉章)特地风尘仆仆地到苏家坨公社看望参加农村“四清”及开展半工半读的师生员工。我陪同吴老参加这一活动后,于5月19日到北京市委报到。已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当天找我谈话,职务是市委书记处的文教书记,分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方面的工作,首当其冲是“文革”方面的事。立即要着手进行的,是接管《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要先摸清情况,清算两报在“三家村”问题上的错误,使报纸尽快以新的姿态投入“文革”之中。6月3日,新华社?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正式公布李雪峰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我和高扬文、马力为书记处书记。我作为文教书记,还兼任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代表华北局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会议。与我这样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还有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东北局)、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西北局)、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代表西南局)。我们这几个人都算不上是“文革小组”的成员,只是边缘人物,且很快都被打倒和撤职了。
我去北京市委报到的前后一两天?大概是5月18日或19日,发生了触目惊心的邓拓自杀事件。邓拓当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他是党内著名的秀才,是党和国家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而今成了“文革”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因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被横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他因不能接受这些罪名,又无法正常申辩,便留下遗书,以死抗争,终年才五十四岁。按说,他的死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应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和警惕。北京市委曾为此报告中央。事后,李雪峰曾传达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想不到批示中毛泽东对此竟风言冷语,很不以为然。对此,惺惺相惜,引起我无可名状的悲凉。应该说,我参加革命后,对于毛主席有出自内心的敬仰、热爱和崇拜,而他对邓拓之死有如此批示,如此的铁石心肠,真使我大感意外。由于毛泽东有这样的态度,作为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在一次会议上,在说到邓拓之死及其遗书时,也轻蔑地说:“邓拓的遗书很恶毒,睁眼说瞎话,用他的行动作出结论。遗书坚持反动立场,说过去的一切与彭(真)刘(仁)无关,实则是坚决的包庇。其次,对所有的批判都反对……”从李雪峰讲话所透露出的邓拓遗书的点滴内容看,邓拓确是宁折不弯的大丈夫。
到北京市委工作后,我参加了原北京市委、市人委副部长以上的所谓“揭发批判彭真及三家村黑帮”的大会。这次会议从5月22日起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的基调是揭发批判北京市委原来主要领导彭真、刘仁、郑天翔的问题,要求与会者勇敢揭发,同时也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原北京市委的一些干部,如崔月犁、张大中、李琪、韩伯平、张文松、宋硕等都曾在会上无可奈何地作过或揭发、或检查性的发言。有一次会议,还专门安排了原北京市委的三位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作检查,以?过关。
作为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我在七十多天的工作过程中,花费精力最多、感到最为棘手的,还是派工作组的有关问题。派工作组的导火线,缘于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副部长宋硕及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和党委副书记彭佩云,扬言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于当时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政治局扩大会的有关情况尚未公布,在此之前党中央、国务院曾经发出过关于贴大字报的指示和规定,如“遵守纪律”、“内外有别”等。因此,聂元梓的大字报张贴之后,既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也遭到了许多北大师生的反击。出人意料的是,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却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随之《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高度评价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因而很快在北京、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当时,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为稳定社会正常秩序,保证“文革”的正常开展,作出了派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的决定。据我所知,在此之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就在5月30日向在外地的毛泽东请示,拟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到?民日报社,毛泽东于当天就表示:“同意这样做。”当时大家都认可派工作组是顺理成章的事,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都未对此提出异议。北大的工作组派出去之后,各方面的情况都紧张起来,各个学校都要求派工作组。一、两天内北京市、华北局和中央工交系统就抽调了四十多名干部,包括中央组织部及其他各部的一些正、副部长,分别到各个大学任工作组组长。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工作,我原以为派出工作组,就可以舒一口气了。但更复杂、更尖锐的斗争还在后面。一方面是一些学校的工作组与所在学校的造反派发生矛盾和斗争;另?方面是中央高层领导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发生分歧。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北京新市委的李雪峰主张派;江青、陈伯达、康生则时刻窥测毛泽东的意图,以求政治投机。他们开始也主张派,后来又看风使舵。我则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斗争的漩涡,甚至成了替罪羊。
1966年7月初,华北局要在北京市召开华北局工作会议,集中讨论“文革”的问题。为此,市委要准备一个大会发言。我和黄志刚根据李雪峰一次讲话精神,先草拟了一个提纲,再由市委简报组起草成文,经过书记处会议讨论,最后由李雪峰、吴德定稿,而后让我在会上代表北京新市委发言,还用市委名义上报中央。这个报告因贯彻了支持派工作组的思想和内容,后来被指责为是“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和典型”。我想,这大概是我被撤销“北京市委书记”的根据。但执行“反动路线”的又何止是我呢?“文革”后期,我有病在家休养时,吴德同志曾到家里看望,我曾问他:“我到底为什么被撤职?”他满脸带笑却吱吱唔唔,没有说出所以然。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