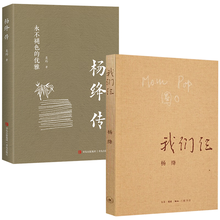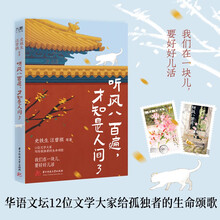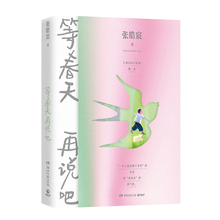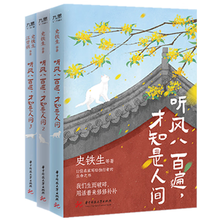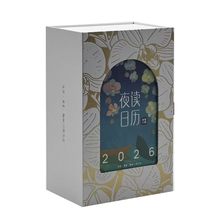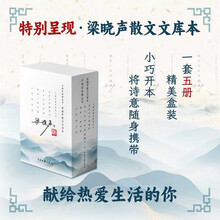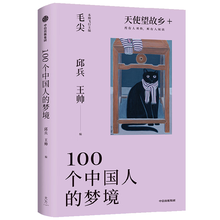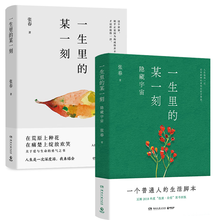季节走到晚秋,正值木芙蓉花期——合肥的护城河畔,公园临水处,居家的老式庭院里,处处可觅芳踪,主旋律一律红白互间,翻卷着,又含蓄着,似乎合不得全部打开自己,宛如隐而不发的心事。
芙蓉花开的时候,又怎能不写写赵佶呢?
每看见他的《芙蓉锦鸡图》,都有温暖的回忆——乡下人家嫁女儿,抬过来一床床喜被花团锦簇,上面绣的正是赵佶这样的芙蓉锦鸡。小时候不大识得花鸟,一直把木芙蓉误认为牡丹,将锦鸡当作凤凰。错误的记忆不打折扣,一样温馨。在乡下,无论婚丧,都一样当喜事来办,无论新床上,抑或棺木上,覆盖的一律是团花的锦被缎面,荡漾着中正平和的古风,一如赵佶的画,都是一脉贯通的,这一脉也长,一径流淌了千年。十一假期回小城参加弟妹婚礼,顺便见着了从枞阳乡下赶来的叔伯姑婶们;饭桌上,二伯忽然轻声告知:你二娘不在了……我恸一下,不知如何安慰。听我妈妈说,患癌的二娘不顾晚期疼痛躺在病榻上,依然吩咐家人应该买回多少串小鞭炮在送她上山的路上放……我惊愕不已,不及花甲之岁,明知大限迫近,却仿佛与她无涉,竟有如此从容之心,像是吩咐别人的后事?到后来,终于明白,那是源于乡下的他们对于生死的一贯通达,把死亡看成了一场远行,也就是所谓的中正平和吧。
赵佶大号宋徽宗,若尚在,我算了一下,到今年,怕也有873岁了。其实他是短命的,比我二娘的年岁还短,仅活了53岁,在靖康二年,被金兵俘获,死于五国城。这个人虽治国无能,但对于书印字画倒见功力,历史上与他一样著名的文人帝相还有一个李煜,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继续说赵佶的画,他是真的把厚朴粗拙与精工细丽紧密团结起来的好模范,一如昨夜余温,厚道有力,涸染着绵延的古意,恍如始终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喜被,古风犹存,最浓烈的披花着色,红也红得方正热闹,绿却绿得意境参差,同时又不失骨子里的中规中矩,是可以拿手指去触摸的可亲可怀,甚至是贴于脸上摩挲的百折柔然。锦鸡歇在芙蓉的花枝上回首斜望,晚秋的光摇摇欲坠,锦鸡美丽异常的长尾羽直曳到地上去,我们似乎看见了秋风轻轻吹过——春天的风一直是浩荡的,长驱千里万里,而秋风始终是有着情怀的,多姿摇曳,细碎,节制,又绵延不绝。画面右上方,两只花蝶翩跹,仿佛两支深秋的哀歌晚唱,其他的都成了蛹埋在地下,只有它俩犹如梦里生动的呓语划破静夜良辰——这么一直看过去,这幅画始终透着一股富贵华丽气,可是,不要灰心,再看右下角,竟塌着肩斜立了一丛菊。菊是白菊,乡野里最普通的族类——正因为有了这一丛菊,便破掉了原先的富贵气,一下变得平和简朴起来,所谓逻辑学上的不破不立。画右空白处有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管。引用别人的话说,就是“诗发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了。底色是黄的,这种黄,既不是璀璨的银杏黄,又非艳嫩的柠檬黄,倘要一定为它命名的话,那也只能是岁月之黄。
这一年观画,自宋元明清这么一路看下来,老画如枯藤昏鸦,其底色似乎普遍带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岁月之黄,都是时光的淬砺洗礼,所以古意凛然,看久了,人不免有些暮气,格外不想说话、动笔,于是,从冬写到春,再从春到夏,转眼又是深秋,依然没有收梢的意思。时间真是美人的脸,禁不起揉搓拿捏,便独自荒芜凄凉起来,更多的时间叠在一起,就成了岁月。每遇到“岁月”这个词,就想起吃石榴,享用着甘美的汁液在舌尖翻滚的短暂,转眼又见苍老干瘪的籽粒,尸一样躺在果碟碗盏里。
到了《腊梅山禽图》这里,赵佶顿时收起富贵华丽的笔融,明显寥落消瘦起来,文人画风显露无疑。大片留白过后,虬瘦的斜枝上略挂梅花四五六七朵,白得惊心耀眼,隔着八百多年的风烟雨尘,仿佛依然闻得到清洁的寒冽之气,宛若一种内在的精神在空气里回荡共鸣。
在赵佶的多幅花鸟中,情有独钟《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可是,后来涉猎资料,偏偏谢稚柳先生将这两幅做了剔除,鉴为伪作,相当扫我的兴。史上一直盛传伪作之说,且各据一词——盖因赵佶在位时,广收古物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网罗画师之故。我这个外行一直少信多疑,且小人之心地认为,持伪作论的人大约是欺辱赵佶的“皇帝身份”罢了——赵佶治国无能,后为金兵所俘,跟李煜一样吃尽苦头。可是,一个人可以受苦,但不能受欺辱。历来最高行政掌官的民生总结报告皆出自身边高级文秘之手的现象昭然若揭,但个别如马英九之流的施政演说,相信应该出自他的亲笔,因为他曾经就是蒋经国多年的高级秘书。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