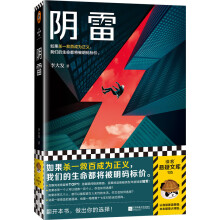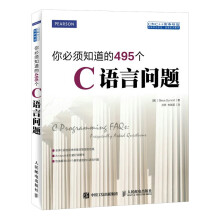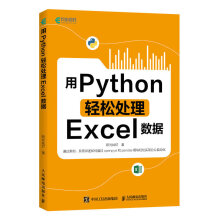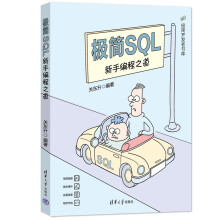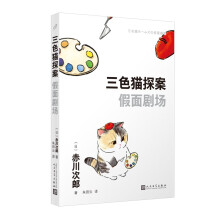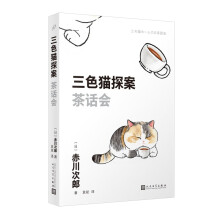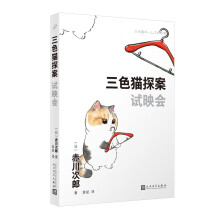墨子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去反对贵族统治者的奢侈享乐是正确的,但主张禁止一切音乐,则是偏激的。他没有认识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对社会、对人的作用。
音乐至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更趋完善,但仍以儒家思想为主。《吕氏春秋》又名《吕览》,为秦国吕不韦召集门下所编,中有专门论乐的文章。其中《古乐》篇对艺术的起源作了几种不同的解释。《音初》篇对各方音调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了论述。《大乐》篇引用了阴阳家的音乐论述,指出音乐要合乎“道”。《适音》篇指出中和之音就适中了。《侈音》篇对统治者过度追求声色,提出了批评。
《淮南子》为汉高祖之孙淮南王刘安的幕客所编。在艺术的审美认识上突出的是音乐。其次是绘画。其最主要的论述是形声的有无之间的关系。认为“有生于无,实出于虚,五色生于无色,五音生于无间”,“视于无形,则得其所见”,“听于无声,则得其所闻”,因此,去追求无色、无声,从而达到“无乐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的审美至高境界。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乐书》一篇,专门论及音乐。他认为音乐的社会功能是“故乐所以内辅臣心而外导贵贱者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故君子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音乐是“养行义而防淫佚”。
西汉经学家刘向在他的《说苑》书中有关于俗乐的记载,可与《乐记·魏文侯篇》互相补充,使我们对古代的俗乐有较全面的了解。
魏晋之际的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其《乐论》是一篇音乐美学的论文。他认为音乐的产生,在于调和阴阳,娱悦鬼神,教化民俗,协调上下,体现了儒家音乐的美乐的思想。和阮籍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其《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重要的音乐美学论文。其中心是“声之于心,殊途异机,不相经纬”。他认为声音只是“自然之和”,人听音乐之所以产生不同的情感变化,不在于曲调内容的本身,而在于人们的主观情感。文中对音乐创作与欣赏方面作了探讨。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其文化也堪称鼎盛。音乐亦如此。唐太宗李世民喜欢书法、音乐。在音乐思想方面他认为音乐上的新、旧、哀、乐的变更与政治兴亡无关,政治上的兴亡,在于人治,对于音乐决定国家兴亡的儒家传统观念,给予有力的批判。从此,“政在人和,不由音和”的观点,成为主导思想。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