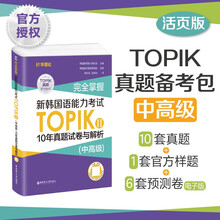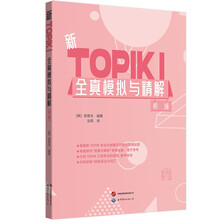沉重的心情和对生活的厌倦,硬生生地拖着我的脚步来到了南浦。
回到京城七八个月毫无规律的生活,不仅使我的全身软绵绵地如同海绵,甚至连我的灵魂也都蚕食殆尽。全身任何一个部位都充溢着酒精和尼古丁的恶臭,我已经如此疲惫不堪。加上经历六、七月的盛夏之后,需要添加衣服的季节来得较为突然,更使我的身体不堪适应,就是在附近散散步,也都会冷汗涔涔,要跟朋友聊天得先备好木枕才行。
但是,极度亢奋的神经却到了临睡前也不得安宁,经常到了公鸡第二、第三次打鸣的时候也辗转不能入眠,直至熬到天蒙蒙发亮时,才勉强能够合一会儿眼。这种状态持续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干脆放弃了关灯上床。
不管是我关灯躺在床上,还是静静地安坐,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场面强烈地刺激我的神经,那就是被解剖的青蛙四肢被针固定在木板上的模样。
在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上博物学实验课的络腮胡子老师在实验室里解剖青蛙后,把还在冒着热气的青蛙的内脏一一掏出,就像放下入睡的娃娃那样小心地放入酒精瓶里,仿佛是有了什么重大发现那样,环顾围在他身边的学生们说道:
“诸位,过来瞧瞧,它还活着呢。”
说完,他就用锋利的针尖逐一拨弄青蛙的内脏,刨去内脏的青蛙就那样被钉在木板上颤动着四肢,仿佛经受着无奈的痛苦。
八年前的那个场面最近重又浮现在眼前,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发出青光的手术刀、不断蠕动的那鸡屎般大小的心脏和肺、针尖、轻微的颤动,这些场景依次浮现在眼前之时,我的头会阵阵发麻,全身像泼了凉水般寒令。
即便是躺在漆黑的屋子里,那朝阳的窗户下高举的手术刀反射出的强烈的反光,好像依然直刺我的眼睛,紧闭着的眼睛好像依然因此而酸涩。每当如此,我就会想起放在床头柜里的刮胡刀,这更使我惴惴不安。
我去南浦之前的夜晚,这种症状变得更加严重。高悬的电灯把小小的房间照得过分耀眼,若关掉它又不无再次陷入到幻影之中的忧虑。但是,我还是打定了主意光着上身,猛地跃起关掉了开关。但是随着“哧溜”的声响透过门缝溜出房门后,络腮胡子的手术刀、抽屉里的刮胡刀重又掩袭而来,占据了我的脑海。手术刀……刮胡刀,刮胡刀……手术刀,越想忘记它们的存在,它们越是黏住我,在我脑际里交相辉映,连绵不绝。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抽屉。
这种怪异的魔力越想去控制它,它就越发不可控制。在睡梦中被抽屉拉开的声音惊醒,睁开眼睛却只有没有关上外门的窗户泛着朦胧的光,房间依然沉浸在黑暗之中。虽然我全身都能被这非同寻常的恐惧所控制,连根手指都无法动弹,但是,另一方面我对那奇特的魅力和诱惑的感受却达到了顶峰。
“我是不是疯了?难道这就是要疯的征兆?”
我为自己的想法所吓倒。
我如同沉醉于睡梦中的汉子,猛地踹开被子跃起,把手伸向了抽屉。但是,在“一旦拿到手就……”的想法雷电一样闪过我的脑际的同时,我仿佛从沉睡中惊醒恢复了精神。我试着要打开电灯,但还是摸索着找到了火柴盒。吱地一声划了一根火柴,拿下并点上了放在窗台上的蜡烛,然后,打开了抽屉。
半途而废并搁置好几个月的原稿、信件、药盒等物就像废纸一样塞满了抽屉,我伸进手去摸索了一会儿,终于触到了刮胡刀滑溜溜的手柄,便转过头取出并从窗口扔到了院子。然而,依然难以入眠。
浑身酸软无力,冷汗涔涔。我就像差点变成尸体的患者,张开四肢软绵绵地躺着陷入了静静的思考。
“无论如何,我也要离开这个屋子。”
我环顾了一下厌倦透顶的房间,这样想道。不管去哪里,几个月前我就有了出游的计划,但也只是说说去夏天曾游玩过一回的新兴寺看看而已,至今也没有付诸行动。
“不管去哪儿,一定要离开这里。走到世界的尽头,无边无际的,永远地,只要是能够走得到的地方……无人岛!西伯利亚荒漠的原野!让太阳晒得滋滋冒油的南洋……啊啊。”
我想起了在某明信片上看到的郁郁苍苍的森林,还有坐在椰子树下的裸体土著人,心中觉得爽快,不禁耸了耸肩。真的想坐上连一分钟也不停留,喘着粗气,挥洒着汗水全速向前飞驰的火车,永远飞奔下去。这是我比任何东西都渴求实现的心愿。如果坐上后,没有产生眩晕的顾虑,也许我就会喊着飞机!飞机!独自一人在那里欢呼雀跃。
几个月都没能出门,囊中羞涩虽然是最大的原因,但真的要迈出大门的确也不那么容易。
第二天,H来找我说今天一定要出发,让我陪他一起同行。这次去平壤可以抛开京城许多烦人的琐事,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此行能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情,仅出于坐火车的好奇心,就爽快地答应“好啊,去,去”。
可是,到了真要出发的时刻,我却举棋不定,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去。总之,我就被H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到了南大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