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间几位老先生的认真给我的印象很深,如今偶尔说给青年教师听,看到他们的无动于衷,便想到,不再是“一个时代过去了”,而应当是“又一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做教师的,应当多看看前辈是怎样做的。
老一代教师上课的认真及魅力,青年一代也许想不到。听唐圭璋先生讲宋词,场面很大,青年教师和硕士生簇拥而人,他坐着讲课,有硕士生代他板书。其实唐先生为人极其平易,实在是年事已高,气力不足,没法亲自书写了。他讲课时,言必有据,面前放着讲稿,但他基本没看,心平气和,就像在书房里与朋友晤谈。系里的老教师说,当年唐先生讲宋词,上课时偶尔还会取出一支箫,吹出很伤感的曲子,一座怃然。诸祖耿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他给我们讲《战国策》时,年已八十。他高度近视,伏在讲台上,用一枚放大镜看着讲稿,边看边讲,连讲一个多小时,根本不在意学生反应;虽然有年轻的学生认为他的课“不好玩”,但也不敢胡来。学校实在是浪费他的生命,不该让他来教本科生的,然而当年动乱甫定,硕士生人数比教授还要少。像诸先生那样的人物,应当说是晚年被耽误了。段熙仲教授,教我们时也已经八十出头了,系里有教师私下里说他是“反革命”、是“地主”,1949年以后吃尽了苦头,平反后,他上课仍是一丝不苟。有一次路遇,我顺便向他请教有关《晋书》中的一些问题,他双手拄杖而立,告诉我:什么问题查哪一本书,某件事在谁的传中,另一本某篇可以参照了看。时间不短了,我担心他老迈,想打住,便推说已经知道了,我回去查书。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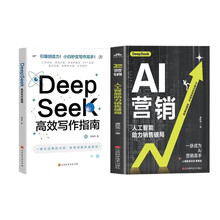





我在病中,想起一个又一个学生的面容,感叹生命的短暂,同时也赞叹生命的美丽。我感谢上天让我有机会认识这些美丽的生命,让我感受他们的仁爱和贤德,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让我知道职业的使命与荣耀,让我敬重生命中的永恒。
——吴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