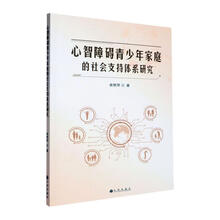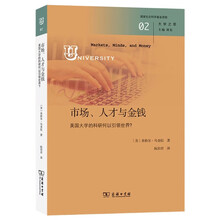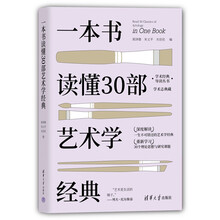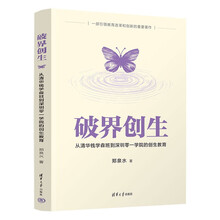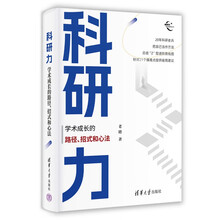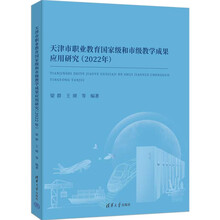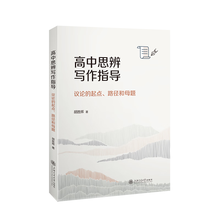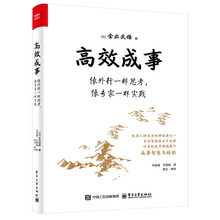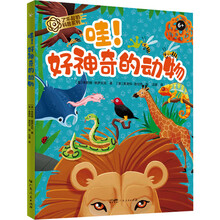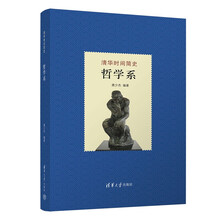洋教习对京师同文馆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如在丁韪良任总教习时,课程由西文和中文等纯语言课转变为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等语言课和数学、物理、化学、法律等十多门科学课程并存。洋教习还组织和参与编译、编写教科书。由于京师同文馆很多课程是首次开设,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此,需要编译、编写大量教材。对于洋教习的贡献,奕诉等朝廷大臣大加赞赏:“历年以来,洋教习均能始终不懈……其各教习训课之余,兼能翻译各项书籍,勤奋尤为可嘉。”(中国史学会,1961:Ⅱ,64~65)奕诉等朝廷大臣也曾奏请对有功之洋教习加以奖励,以资鼓励。光绪十一年十一月(1885年12月)奕诉等朝廷大臣奏请赐总教习丁韪良三品衔,法文教习华必乐四品衔,化学教习毕利干四品衔,这些教习“资格最深,馆课亦能勤慎”,所以“拟请赏给虚衔,以昭激劝”。其他各馆洋教习都有出色人选,“其余尚有英文、俄文、天文、算学、医学各馆洋教习,俟有成效”(中国史学会,1961:Ⅱ,65)。
然而京师同文馆的洋教习良莠不齐,有勤勉者、教有成效者,也有督学不利、教学无方者。后者在京师同文馆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晚清政府初次开办学馆,招聘洋教习,未免经验不足。京师同文馆曾一度由外国人直接负责,缺乏晚清政府有效的监督。虽然派遣了政府官员或聘请中国教习从旁辅助或兼管,但由于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京师同文馆的洋教习往往依照自己的方式处理新式学堂中的语言和其他课程的教学。其次,洋教习聘请的标准不明确,没有对其专业提出相关要求。另有部分洋教习来京师同文馆的目的与办学目的不一致,导致了京师同文馆一些问题的出现。
京师同文馆自开馆以来,一直延请了本国人担任教习,这些汉教习是通过考试的方式择优录取到京师同文馆担任教学任务的:“请于直隶、河南、山东和山西四省之候补八旗教习咨取考试,挨次传补。”从这四省考选教习主要是因为他们“语音明白,易于教授”(宝鋆等,卷五十九,1930)。投考人员由礼部咨送。然而,四省中八旗教习无人前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遂调整了汉教习的任用方式,“将咸安宫、景山等项候补教习均准一体考试”(宝鋆等,卷五十九,1930)。有的教习并没有经过礼部咨送,但由于自愿投考,考虑到无人投考可能导致人员短缺,所以予以录用。后来奕诉等朝廷大臣建议将投考的汉教习条件进一步放宽,取消了地域限制,也不局限于八旗:“拟请嗣后无论何省,凡系举贡正途出身,俱准取具同乡京官印结,赴臣衙门具呈投考;其在部之候补教习,如有愿考者,仍准礼部照章咨送,通由臣衙门汇齐考试,择其文字优长、语言明白者,详慎录取。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