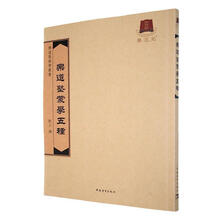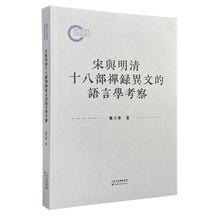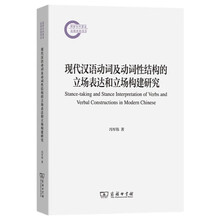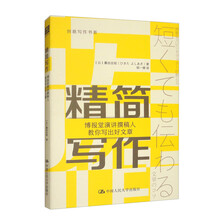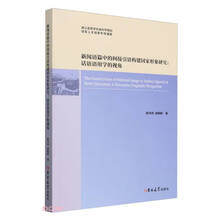前面一节讨论的在语义上引入施事论元的“中动结构”,也有人说其实那不过是非宾格动词结构本身的一种句法语义表现。即“致使类”非宾格动词结构中客体名词做宾语时,结构中原本是有施事外论元的,如“船员沉了船”(船员使船沉)、“门卫开了门”(门卫使门开);而当客体论元提升做主语时,如“船沉了”、“门开了”,施事外论元就被强制“删除”或“抑制”了(潘海华、韩景泉2005)。这种说法显然有缺陷:因为既然是“非宾格动词”,那么结构中就只能有客体内论元,不会有施事外论元,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施事外论元的删除或抑制;即使客体名词做宾语时结构中还可以补出一个主语名词,那也只能是领有成分或处所成分,不是施事外论元。例如在“父亲死了/王冕死了父亲”、“狗熊跑了/动物园(里)跑了只狗熊”里的“王冕、动物园”就是如此。因此一旦某个非宾格动词结构中出现了典型施事论元,那么只能说是这个动词“兼有”了一般及物动词用法。前面说“跑”这类非宾格动词加上“给”只能引入语义上的外论元(外力),如“狗熊给跑了”;而“沉”这类非宾格动词加上“给”却可以再加上句法上的外论元(施事),如“船给船员沉了”,也证明了这一点。
非宾格动词结构中本来就没有施事外论元,所以不可能存在施事外论元的删除或抑制,但反过来本来带有施事外论元的结构,虽然施事论元的语义在动词论元结构中是永远不能被消除的,但这个施事论元在某种结构条件下不能再出现词语(即失去句法位置)却是可能的,这也才是施事外论元的一种“抑制”现象。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