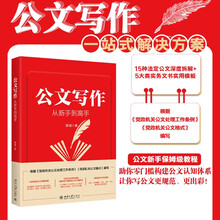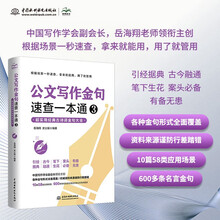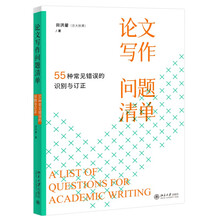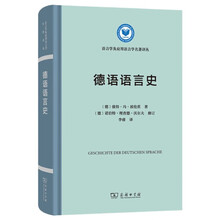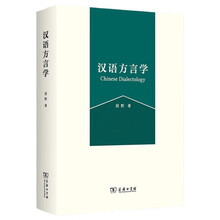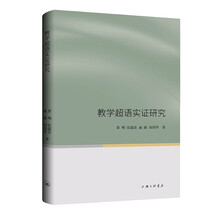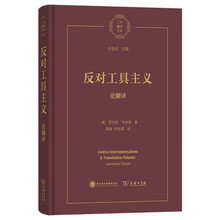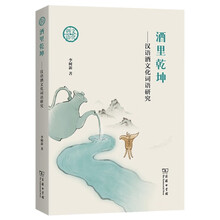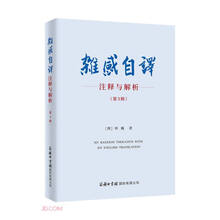1.2 观点之二:天津话的底层是冀鲁官话,后受北京、东北、胶辽官话影响
王临惠、蒋宗霞、唐爱华最近(2009:45-50)认为“天津方言来自淮北平原的宿州、固镇一带的方言的说法证据不足”,作者通过安徽宿州、固镇方言的田野调查并与天津话语音进行比较,同时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得出结论:“天津方言的底层是冀鲁官话,但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北京官话、东北官话、胶辽官话的影响。”文章的具体理由如下(王临惠等,2009:46-50):
(1)天津话的声调格局与宿州话没有血缘关系;
(2)天津话知系声母读音老派同东北话官话和固镇方言,新派属东北官话的长春型;
(3)天津话宕江摄入声字的文白异读与冀鲁官话、北京官话的同步发展,其底层不可能是淮北平原的方言;
(4)明初洪武年间安徽淮北一带人口稀少,根本就没有向外移民的条件;永乐初天津三卫戍卒的来源并无文献记载。
就基本研究方法而言,上述两种代表性观点都是经过历史文献的考察、天津话与安徽宿州话语音的比较而得出来的,但是结论却相对立,问题在哪里呢?
第一种观点“天津话源自以安徽宿州为中心的淮北方言”(李世瑜、韩根东,1991)发表时间较早,影响比较大。但是,用以支撑文章观点的明初人口、来源等理由仅是依据传说,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再者,作者仅凭语感认为天津话与宿州话是同一方言,缺乏细致的语言分析,且未提及天津话与宿州话的入声归派规律明显不同等差异,而这是源流问题讨论不能回避的。因此,不少学者对此观点存有疑虑。
第二种观点“天津话的底层是冀鲁官话,后受北京、东北、胶辽官话影响”(王临惠等,2009)的论证从语音特点的比较入手,强调天津话与冀鲁、北京、东北、胶辽官话的相同点,列出了一些微观现象。但是,作者未对天津话与宿州、固镇话声调的接近作出解释,亦未解释为什么天津话在周边方言里显得“另类”的问题,文中的文献考察分析及所得观点尚可商榷。
总之,提出上述两种代表性观点的文章均有不少值得肯定借鉴的学术价值,为天津话来源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不过,近代天津移民的来源究竟如何考察,天津方言特点中哪些是源哪些是流,两篇文章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存在分歧和较多的补充空间,这也是导致各自得出不同结论的因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