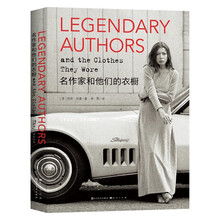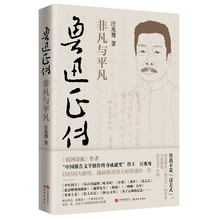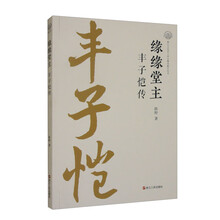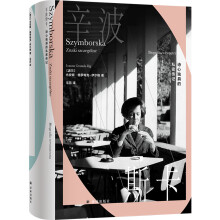第一卷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br> 第一章 “一个星斗满天的黎明,我出生了” <br> 如今,人们普遍把1564年4月23日当做威廉?莎士比亚的生辰,这一天正好是圣乔治日。然而事实上,他可能是在4月21日或者22日出生的;不过不管怎样,人们恰好选择这个举国欢庆的节日作为他的生日,也是出于一种冥冥之中自有巧合的心理,并没有什么不妥。<br> 在产婆的帮助下,这位16世纪的天之骄子离开了母亲的身体,降临到滚滚红尘。产婆帮他洗了个澡,用一块柔软的布料把他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襁褓”),然后抱到楼下,让做父亲的看一眼。两人交换了几句礼节性的祝福和致谢之后,产婆又把孩子送回那个温暖、昏暗如旧的产房,放在他母亲身旁。这位母亲想在幼子被放进摇篮之前,让他与自己一块躺一会儿,以便“把他所有的病痛都引到自己身上”(注1)。按照许多地方的惯例,大人们一般会在初生婴儿的嘴里放一点黄油和蜂蜜;不过在沃里克郡,当地的风俗是让婴儿抿一点兔脑制成的肉糜。<br> 莎士比亚受洗的日子不像他的生日那么扑朔迷离:确切时间是1564年4月26日,那一天是星期三,地点就在斯特拉特福的圣三一教堂。在登记时,教堂的神职人员用拉丁文写下了“约翰?莎士比亚之子威廉”(Guilelmus filius Johannes Shakespere)的字样,这里他出了个笔误:名字当中的“Johannes”其实应该写成“Johannis”。<br> 父亲抱着出生才几天的莎士比亚,从位于亨利大街的家里出发,穿过高街和教堂街,来到教堂。母亲没去受洗现场。陪同约翰?莎士比亚和他的新生儿一起上教堂的很可能是孩子的教父母。小莎士比亚的教父名叫威廉?史密斯,他是个裁缝,也住在亨利大街。孩子的名字在洗礼仪式开始前得到正式确定。在洗礼盆边,教父母受到训诫,他们必须保证威廉?莎士比亚在以后的岁月里能够经常聆听布道、学习教条以及“用英格兰语言”颂出的主祷文。洗礼结束后,人们把一块白色的亚麻布盖到孩子身上,这块布要一直保留到其母亲做完“洁净礼”后才能拿开。这块布也叫做“洗礼布”,如果婴儿在一个月内夭折,它就是孩子的寿衣。在伊丽莎白时代,尽管英国国教经过改革,但是在洗礼仪式上,教父母还是喜欢给婴儿送门徒汤匙或洗礼衫;参加洗礼的人还要分吃洗礼蛋糕。家人为了庆祝和期盼幼小的威廉?莎士比亚永得救赎,也让他经历了这样一个繁琐的洗礼仪式。<br> 然而,小莎士比亚在现实中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16世纪,新生儿的死亡率非常高,9%的婴儿在出生后一周内夭折,而11%于满月前离开人世。(注2)在莎士比亚出生的60年代,斯特拉特福平均每年有62.8个婴儿受洗,却有42.8个孩子举行葬礼。(注3)那个时候的孩子要想幸存下来,要么得非常健壮,要么就需出生在相对富裕的家庭,莎士比亚很可能这两点优势都具备。<br> 但在那个年代,即使人们成功跨过了孩提时代的种种危机,接下来还要面对一个更大的挑战。当时,成年男子的平均寿命是47岁,就这个标准而言,莎士比亚的父母都可谓长寿。按照常理,莎士比亚本人也应该有望至少活到父母亲的那个岁数,然而他最终只比平均寿命多活了6年。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在伦敦,即使是富人区的居民,平均寿命也只有35岁,而贫民区的人们更是只有25岁,因此城市很可能就是让莎士比亚相对短寿的杀手。如此低的平均寿命带来了一个必然结果:伦敦人口的一半都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由此形成了十分年轻的文化,到处充满了勃勃生机和雄心满怀的人们。那时的伦敦似乎是一座会永远年轻的城市。<br> 出生仅3个月后,莎士比亚的生命力就迎来了第一次考验。1564年7月11日,教区记录簿上记录了一名高街纺织学徒的葬礼,这条记录的旁边还写着这么一句话:“今日瘟疫爆发。”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大约237位斯特拉特福居民相继离开人世,这个数字占该教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亨利大街上,与莎士比亚家同一边的有一户四口之家,在这场灾难中全家人无一幸免。不过莎士比亚一家成功躲过了这一劫。莎士比亚的母亲很可能带着孩子跑回了娘家——一个位于威尔姆科特附近的小村庄,并在那里一直待到危险全部过去。留在镇里的人大多数受到感染。<br> 小莎士比亚本人对危机没有什么意识,但他的父母亲却饱受担惊受怕的煎熬。这对夫妇早先已经失去了两个女儿——都是在襁褓时期就夭折了,再加上小莎士比亚是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因此他们对这个幼子的关爱和照顾肯定是加倍体贴入微的。一般来说,在这种呵护下长大的孩子,日后都会自信而且乐观,他们会觉得,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上天的垂青和眷顾,世间的艰难统统于他们无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时伦敦经常爆发疫病,但莎士比亚从来没有受过感染。他无疑是幸运的,接下来,让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幸运儿成长的那片土地,或许可以借此帮助我们了解他以后逐渐形成的各种性格特征。<br> 第二章 “她是我生命的精华”<br> 许多人常常用“古朴、原始”等词语来形容沃里克郡,这里绵延的土地和如今已经光秃秃的山峦的的确确吐露出一些古老的气息。另外还有些人把它描述成英国的心脏,其言外之意就是,既然莎士比亚体现了大英民族价值的核心,那么孕育了他的地方也应该在整个国家中占据中心地位。莎士比亚是核心中的核心,是英国特性的内核或源头。<br> 斯特拉特福四周广袤的乡村地区分为两大片地带。北部坐落着古老的阿尔丁森林,在远古时期,这片森林曾经覆盖整个米德兰地区(英格兰中部),人们把这片广阔的地带称作威尔德地区。提起“森林”二字,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树木葱郁、连绵不绝的林地,然而在16世纪的阿尔丁森林,情形并非如此。这时的阿尔丁森林里散布着星星点点的农场、农舍、草地、牧场、荒原以及这一丛那一片的树林。在这个地区,人们看不到房屋相邻、街巷纵横的景象。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地形学家威廉?哈里森的话说,这里的房屋“极其分散,每家每户的生活各成一统、互不干扰”(注1)。到了莎士比亚在阿尔丁森林里徜徉的时候,人们建造新房屋的热情不断高涨,对木材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因此森林的面积迅速缩小。每建造一所房屋需要60到80棵树;此外,开矿和垦荒等行为也让森林遭到不小的劫难。著名地理学家约翰?斯皮德在为其1611年出版的《大英帝国地图集》收集素材时考察过这个地区,他注意到,“森林明显遭到巨大破坏”。英格兰从来就不是森林的天堂——它们总是不能逃脱被摧残的命运。<br> 然而不管怎样,这片森林一直以来都是野性与反抗的象征。在《皆大欢喜》、《仲夏夜之梦》、《辛白林》、《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等作品中,阿尔丁森林代表着浓郁的淳朴民风和远古的记忆。广袤的阿尔丁森林曾是一些古代不列颠部落的庇护所,古罗马帝国侵入英国时,这些部落的人们纷纷躲进森林,得以免遭浩劫。“阿尔丁”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从凯尔特语单词演变而来的,意思是“树木茂盛的深谷”。在法国东北部与比利时交界处有个地区叫做“阿尔丁尼斯”,那也是凯尔特人起的名字。后来,当从赫威加斯来的萨克逊部落四处掳掠时,凯尔特人再次躲进了阿尔丁森林。莎士比亚在孩提时期总是听到大人们讲《沃里克的盖伊》的传奇故事,传说中的这位勇士藏身在这片森林中,率领手下抵抗当年入侵英国的丹麦人,据说他作战时使用的宝剑还曾存放在沃里克堡供人们瞻仰。<br> 阿尔丁森林既是个极佳的藏身之所,也是一个适合劳作之地。许多逃犯和流民纷纷潜入这片地带,一旦到达此地,他们就可以逃脱追捕;不过这也正是空旷地带的居民瞧不起林中居住者的原因。这些丛林居民都是些“生活习惯、言谈举止都不上档次的人”(注2);他们“对于上帝和文明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与异教徒中的野蛮人相去无几”(注3)。在这里,反抗侵略的历史,与野蛮不开化以及可能聚众叛乱的历史,全都交织在了一起。这样的历史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两者已然无法割裂。在《皆大欢喜》中,小丑试金石进入这片土地的时候,大声宣称:“哦,现在我到了阿尔丁森林了。我真是个大傻瓜!”莎士比亚的母亲就叫玛丽?阿尔丁,他后来的妻子安妮?哈萨维又居住在这片森林的外围地带,因此,他从内心深处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而又浓烈的感情。<br> 威尔德地区以南,即沃里克郡的南部地带,是菲尔登地区。在1576年刊行、萨克斯顿绘制的《沃里克郡地图》上,人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只有零零散散的几处小树林。其余大部分地区被改造成了灌木林和牧场,以及绵延在层层山峦之间的耕地。威廉?卡姆登在其著作《不列颠志》中,把这个地区描绘成“平原地形,盛产玉米,绿草成茵,景色优美,令人愉悦。”当约翰?斯皮德站在厄齐丘山上(卡姆登也是在这个位置考察菲尔登地区的)观察这个地区时,他看到“草原牧场披着绿色盛装,上面点缀着点点花丛”,这是一幅英格兰乡村的经典画面。在莎士比亚眼中,这个地区的景致与北方的森林相比不遑多让。一直以来,许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菲尔登地区非常富庶,是新教徒的地盘;而威尔德地区则比较贫瘠,是天主教徒的聚居地。这种看法勾勒出了当时一个深入人心的大众偏见,但是它也反映了一种对立平衡,而莎士比亚天生就具有把握这种平衡的能力。<br> 斯特拉特福地处威尔士山的环抱之中,气候温暖湿润。这一带空气十分潮湿,土地水分充足,斯特拉特福境内就有好几条小溪穿过。西南风吹来的云朵往往意味着即将下雨,当地人称这些云为“赛弗恩?杰克斯”。而只有当“蛮横的北风”到来时,用《辛白林》里伊摩根的话说,才会“摧残我们所有的心花意蕊”。<br> 不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些景致对莎士比亚到底有什么影响,或者说莎士比亚与这样的景象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呢?莎士比亚之后的一些天才地形学家用“区域强制理论”来解释上述问题。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摆脱不了他们出生和成长之地的影响,每个地区的特点决定着其居民的本质特征。不管该理论是否放之四海皆准,单就莎士比亚来说,我们还是可以大胆下个结论:此理论用在他身上十分恰当。他的所有作品都毫不含糊地证明:他不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他的作品没有出生在面包街的约翰?弥尔顿的那种尖锐和雄辩;没有在威斯敏斯特中学受过教育的本?琼森的那种晦涩;没有从伦敦城里来的亚历山大?蒲柏的那种尖刻;也没有住在梭霍区的威廉?布莱克的那种偏激。自始自终,莎士比亚都属于乡村。<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