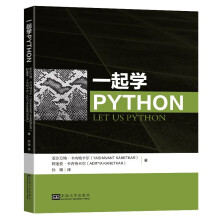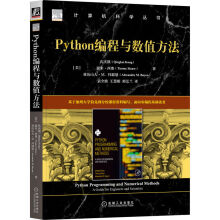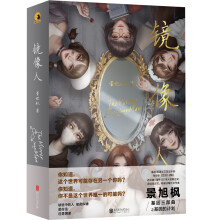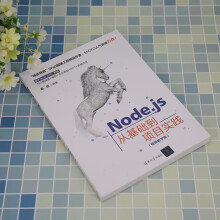一九六九年的一月到九月底,我在美国总共住了有四、五个月,去了两次或三次,我记不太清了。七月份,我去马德里会布努艾尔,我们开始构思《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当时还是草创阶段,还没有定下后来这个名字。写这个本子用了我们两年的工夫,一共出了五个不同的版本。
世界上的这几番风波过后,布努艾尔虽然无意背弃反抗的初衷,但也在探索新的方法;他不想再做无谓的寻衅和抗议,而是反过来摸索着,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把现实表现得扭曲而古怪,开一些扰得人不自在的玩笑,这被罗伯特·伯纳云称作“甜蜜中的颠覆”。
我们起身与世界抗争,然而世界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那就再寻新路吧,换一种方法试试看。
在纽约,我们又见到了约翰·克莱恩、海拉蕊、凡森,以及别的朋友们。玛丽一艾伦·马尔克正在罗马,在费里尼的《爱情神话》拍摄景地拍工作照。她回来以后,就再也没离开我们。
在阿勒公坎饭店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就搬出来了。我们在市中心离华盛顿广场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栋小楼,觉得挺适合。它的地址是乐洛街7号半。我们很喜欢这个“半”。半个号,就好像我们只有一半在美国。
进门先是一条昏暗的过道,被叫做“耗子洞”,走到头就看见两棵细瘦的树,长在一个狭小又少有阳光的院子里。房子是砖房,上下一共四层,每层只有一个房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