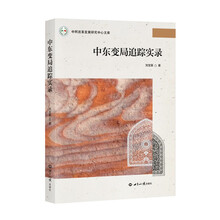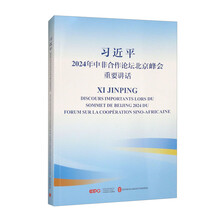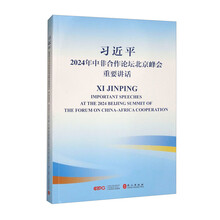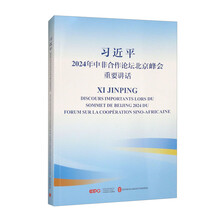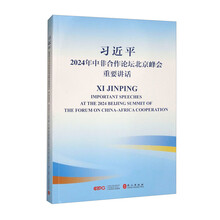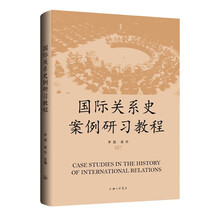1973年5月,我在联邦总理勃兰特当时的官邸第一次同苏共总书记勃列 日涅夫见面。这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而同时又善于政治谋算的大俄罗斯人 ,和一个虽然头脑冷静但又并非毫无情感的北德意志人之间建立一种非常 特殊的个人关系的开端。当时,勃兰特举行一个小范围的非正式晚宴,只 有10至12个人参加。由于勃兰特和勃列日涅夫以及双方外长谢尔和葛罗米 柯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多次见过面,这次谈话进行得比较轻松并且是非正式 的,尽管谈话是断断续续的,因为要逐段进行翻译而不得不一再打断。逐 段翻译,不可避免地要中途停顿,使人有时间仔细整理自己的思想。这使 谈话失去自发性,但却增强了明确性。 在晚宴进行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情不自禁地做了一番独白,诉说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他是故意这样做的,还是出于一时 的感情冲动,我至今没有弄清楚。他谈到,特别是在乌克兰,人们所受的 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当时他在那里担任第18军的少将衔政委。勃列日涅夫 越说越激动,他动人地描绘起遭受损失的许多新的细节、战争的恐怖以及 德国人犯下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他不断地把这些德国人称之为“法西斯 大兵”或“法西斯入侵者”。 我也经历了这场战争。我明白,他是多么有道理。我也明白,他这样 讲是有根据的,尽管他在一些地方有意夸大其词。维利·勃兰特和在场的 其他德国人一定有类似的感触,因为我们大家都满怀敬意地倾听他的长时 间的诉说。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用意是使东道主感觉到这个巨大的转折 ,感觉到他和俄国人为了决心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合作,为了签署莫 斯科放弃武力条约和四国柏林协定,以及为了到波恩来访问昔日的敌人, 作了多大的自我克制。 当勃列日涅夫在作这种描绘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战争年代,这是 30多年前的事了。我回忆起塞契夫卡村燃烧时散发出来的气味和道路两旁 的尸体,我所在的防空营曾不时地接到命令,用两厘米口径的高射炮射击 一些村庄,使之起火,以便把躲在村子里的敌对的抵抗战士驱赶出来。我 记得,有一次当我在后方的一个后勤供应基地看到一卡车俘虏所受的非人 待遇时,我是多么的不理解和惊愕。我也回忆起上级关于处置政委的命令 ,虽然我们不一定亲自看到这一命令执行的情况,但对这项命令将被执行 ,即被俘的政委将被枪决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想起了当时我们都害 怕同被俘的俄国士兵接触,我重又想起了,1941年入冬以后,我们不得不 到房子里寻找地方睡觉——德国人睡地铺,俄国人睡火炕——当时德国士 兵和俄国老百姓都相互害怕对方。我忆起了当时我们自己的惊恐情景,忆 起了一位下腹部受重伤的战友临死前令人惊恐的可怕的叫喊声。从遗忘中 重新唤起了我当年失魂落魄的恐惧:1941年12月,我们在克林附近被切断 和包围,面临被俘的危险。勃列日涅夫说得对:战争是可怕的,是我们德 国人把这场战争引入到他的国家。 但同时,他的片面性却是不对的。不仅德国士兵,俄国士兵也对他们 当时的敌人犯下过暴行。而且,如果他把过去的德国士兵都看作是法西斯 主义者,那他就错了。正如我们当年的敌人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一样,大 多数德国士兵,他们的军士、军官和将军并不都是纳粹分子。双方都以为 是在为祖国服务并且必须保卫祖国。人们早就知道,双方的司令官都是冷 酷无情的。勃列日涅夫单单控诉希特勒,难道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 斯大林也曾把他的某些敌手搞掉了?我丝毫无意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勃 列日涅夫也没有理由谈论苏联的战争罪行。尽管如此,我仍决心加以反驳 。 不,实际上不是反驳,而是向他和他的陪同人员展示这场战争的另一 面。勃列日涅夫大概讲了20分钟。我轻声地、谨慎地开始叙述我的观点, 但我讲了几乎同样长的时间。维利·勃兰特悉听一位前德国士兵其便,而 这个士兵不久前还掌握着对联邦国防军的发号施令权。 我承认,勃列日涅夫说得很有道理,但我反驳了他关于法西斯士兵的 说法。我陈述了我这一代人的情况:我们中只有很少人是纳粹分子并且相 信“元首”,这些人是例外。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到有义务执行军 事上司的命令,而这些军事上司也是同样的想法,他们中间也只有很少人 是纳粹分子。事实上,我在国防军里当兵的八年中,我的上司或指挥官没 有一个是坚信不疑的纳粹分子。不过,我当时被教育成了一个爱国者。 我提请勃列日涅夫注意那些一方面作为爱国者曾同敌人作战,另一方 面又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他们愿意谋反,但不愿意叛国。我谈到那些被炸 毁的城市里人们死亡的情况,以及在逃亡和被驱逐时的苦难,谈到我们在 前线时连续几个星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妻儿在家里是否还活着。我们在夜 里诅咒希特勒和战争,而在白天又在尽我们作为士兵的义务。我向我们的 苏联客人说明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德国士兵是如何在精神分裂的状态下经受 了这场战争和经历了种种苦难。 这一切对勃列日涅夫是否都是新鲜事,我无法判断,但我可以看出, 他注意地倾听了我的陈述。这次对战争痛苦的回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相互尊敬。从1974年我第一次去访问他,到1982年他逝世和我离开联邦 总理的职位,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以这种相互尊敬为特点的。在这八年中 ,我们曾有两次或三次提到1973年5月那次谈话。1980年夏,当我在克里姆 林宫一次气氛相当紧张的会见中提到“总书记先生,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 ”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由自主地打断我说:“这是真的。” 1973年,在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我在联邦政界已经从事了20年的工 作。作为联邦议院的议员、议会党团主席和国防部长,我对世界已有一定 的了解,包括历史上俄国的发展和当前苏联的实力政策作用。不论是1967 年大西洋联盟按照哈默尔报告通过的西方双重总战略,还是1968年以后里 查德·尼克松对苏联实行的限制军备政策,或者是1969年秋维利·勃兰特 当上总理后开始执行的东方政策,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新的考虑。相反, 我在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设想,这反映在我在联邦议院和我党党代会上的 发言中,反映在我的关于战略问题的两本书中以及我作为北大西洋联盟部 长理事会成员的言行中。P1-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