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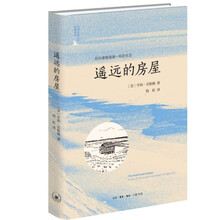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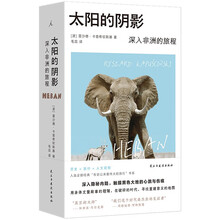
王小慧:亲爱的爱迪特,我们已经认识二十年了!虽然我们见面次数很多,但每次见面总有许多事情要说,每次都没机会真正好好聊聊。其实我一直想请你讲讲你的故事,我很好奇,今天终于有时间了。谢谢你。
爱迪特:我也很高兴接受你的访谈,我的故事很多,你想听些什么?
王小慧:听说你童年经历了战争的惊慌和恐惧,你的离奇故事从那时就开始了,那我们就从你童年开始聊吧。
爱迪特:是的,你说的没错。我们就从我的童年开始聊吧。我1939年1月12日出生,不过那时候二战还没开始。正如后来我所知道的那样,那年九月,因为我父亲要参战,所以我的洗礼只得匆匆完成。教父明显没怎么好好准备讲话,他把我说成是“祖国的儿子”。直到他给我起名叫爱迪特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匆忙之中搞错了我的性别。那时候女孩子无足轻重,“祖国的儿子”才是一个家庭的骄傲。
王小慧: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重男轻女,到我父亲为止,我的祖辈都是“长子长孙”,我祖上有不少值得自豪的先人,唯独到我这代是个女儿。还好我父亲向来以女儿为骄傲。我的时代也提倡男女平等了。你现在是慕尼黑市第一夫人,但你并不是在慕尼黑出生的,而是在德国最北边,靠近波罗的海的基尔出生的,是吗?
爱迪特:没错,我的家原先和慕尼黑没有半点关系。我的母亲来自萨尔州,父亲来自柏林。
王小慧:那你的父母怎么去了基尔呢?与战争有关系吗?你对战争还有印象吗?
爱迪特:我父亲是名海军军官。战争开始前,就驻扎在基尔,于是我母亲和我三岁的哥哥就搬到了那里。我出生在基尔的海军野战医院。后来父亲被派到首都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部工作,我出生后在柏林度过了五年的光景。那时候我们住在里特希菲尔德区一幢狭小的双门联体房里。我的童年最初与战争无关,而是在“玩打仗”。路上到处是一堆堆准备用来加固路面的铺路石,我们就在石块后面闲聊,玩“高射炮”游戏,我们朝天上扔石头,好像这样能打中飞机似的。那之后没多久,我们就真的体验到了战争不是闹着玩的。柏林被炸了,夜里一听到警报声,我们就得马上冲到防空洞里躲起来。我们坐在受到惊吓而哭泣的人群当中,一直等到空袭结束。从防空洞出来以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看到那些房子被炸了。
一天夜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屋里睡觉,父亲突然叫醒我,把我抱到窗前,指给我看:“柏林着火了!”。但当时他一点也不惊慌,而是非常镇静地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真正的男人气概。那一夜的天空通红通红,这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大火。
大人总认为孩子会特别敏感,其实并非如此。当窗外的大火已燃成可怕的景象时,我并不清楚眼前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我还无法理解一座着火城市的不幸。最多就是认识了火的危险,我开始感觉生活不再那么安定了。
大人们还觉得孩子在防空洞里会害怕,可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相反,只有当我看到大人的反应时,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多危险。舅舅在斯大林格勒牺牲了,当母亲换上黑色衣服痛哭时,我才渐渐知道,一个模糊的难以捉摸的危险正向我们一步步逼来。亲人的突然消失使得家中的幸存者深陷恐慌和悲痛。当时我们不知道,大家都很喜爱的舅舅其实并不适合打仗。舅舅阵亡了,我外公最终得到的只是装有他骨灰的邮件包裹,外公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死亡之路,这件事的阴影他始终无法摆脱。
接下来的几天里,柏林不断遭到轰炸,我更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那时,我们必须穿着衣服睡觉,以备随时冲向防空洞。我意识到,我们已身处危险,不可能再过正常的生活了。一夜的轰炸过后,我们看到到处是被炸毁的房子和烧尽的废墟。花园也被炸坏了,眼前的一切特别触目惊心,透过一面残缺的墙看到一问有架钢琴的完整卧室,它兀自矗立在那里。我突然想到,这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家,我的房间,这让我非常害怕。此外,那些被炸死的邻居,那些坐在残缺不堪的房子旁和破损汽车前哭泣的人们,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在接下去几个轰炸的夜晚,我向天空祈祷,希望我们能够在这场厄运中不受到伤害。当听到从前线传回邻居的男人们阵亡的讯息,当听到孩子们的哭诉,这是最难过的时刻。眼前展现的是一片深渊,让我不再理解这个残酷的世界。
后来我们去了萨尔州的外公外婆家,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那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切如同往常一样井然有序。路上到处都飘舞着纳粹旗,游行队伍不断,有时还会经过家门口。我们看到邻居家的小伙伴弗里茨(Fritz),我哥哥欣喜地说:“啊,弗里茨也参加了!”他指的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游行和演习。这样一个游行演习深深吸引着男孩子,这支身着军装的队伍看上去充满活力,令人羡慕。男孩子都想参与其中,而不是做旁观者。军队的乐曲听起来让人激动,各种体能训练让男孩更显健美和阳刚。我的哥哥为此感到非常骄傲,连三岁的妹妹也能说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复杂绕口的希特勒党派的名称。
王小慧:你的父亲作为海军军官,是在第一线作战,还是像一名高级官员在海军总司令部工作呢?
爱迪特:一半一半。他在军舰上执行任务时,我们几个月都看不到他。他在柏林总司令部时,每天晚上都能回家。他在那里是海军上将和最高指挥官的副官,他非常自豪能够这么接近舰队的最高统帅,他觉得这非常重要。每天早晨他穿着军装离开家,晚上也是这样回来。我曾一度觉得他只是在展示他漂亮的军装,我对这个印象并不深,只觉得他对一切都非常严格,甚至很刻板,刻板到难以忍受。有时,他在家也会谈到军事行动或者和其他军官的一些惊险遭遇。我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我的哥哥却听得津津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