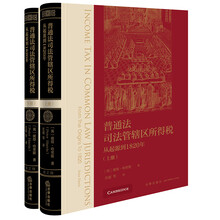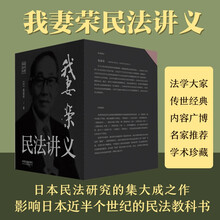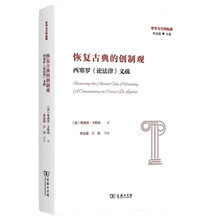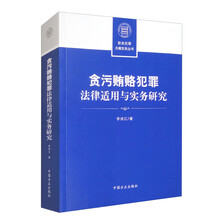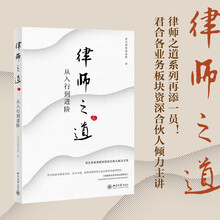法律现象的复杂性、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决定了立法语言必须使用模糊词语。现实生活中,有些法律现象本身边缘模糊、分界不明,剪不乱理还乱;还有一些法律事物(现象)在人们的主观世界中边界是模糊的。如果将前者称作客观的模糊事物,那么这后者便是主观的模糊事物。表达这样的模糊事物,无论是客观的模糊事物,还是主观的模糊事物,别无选择,只能使用相应的模糊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且不说其中的“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本身就是语义边界模糊的词语,但说“显著轻微”和“轻微”之间、“不大”与“较大”之间也还有一个定位与分界的问题。由此而来的问题是:那些介于“显著轻微”和“轻微”之间,即比“显著轻微”重,又比“轻微”轻的违法行为,算不算犯罪?是归于“罪”,还是归于“非罪”(姜剑云,1995)?这可是让法律人士挠头的问题。然而,这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事物本身就是这样模糊,因为人们的主观认识就是这样的模糊。
其次,立法作为认识过程要受到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美国语言学家sapir在他的《语言》一书中写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这些做法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sapir.E.,1921)”。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社会是一个以“礼”为纲,讲究自然血亲的宗法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人是不被重视的,甚至是被否定的。个人被隐埋在家、国里。而国即君,君即国。这种社会关系就衍化出一种个性压抑、思维内倾的世风。在这种世风的影响下,人们在认识法律现象时,往往满足于通过直觉得到一个总体印象,而不习惯于作周密详细的分析,这与立法语言讲究逻辑严谨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国立法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针是“宜粗不宜细”,由此导致了现行法律中出现了大量的模糊性语言(焦悦勤,2005)。
再次,立法是立法主体依照职权和法定程序对社会法权关系进行认知、把握和表述的过程。首先,立法者视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而社会公共利益又是多元化的,不同的立法主体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立法的利益机制问题,最终立法者只能基于一定的立法意旨,运用价值判断,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有弹性和伸缩性的语言,也就是模糊语言。其次,立法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社会工程。立法技术对立法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在制定法律时,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立法者在某些情况下会有意使用模糊性语言,如在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等刑法条文中,为了防止将国家机密泄露,保护公民名誉,立法时便选择一些模糊语言来表述有关法律内容。
最后,从立法目的转化为法律规范的过程同样要受到各种客观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法律规范是通过一定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而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思想的物质载体和表达工具有时却难以充分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相同的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不同的语词在相同的语境中却可能有着相同的意义。语言符号系统“所指”与“能指”是不一致的,是有裂缝的,有时候达到二者几乎完全脱节的地步,二者很难达到同一关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