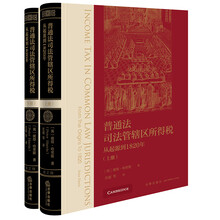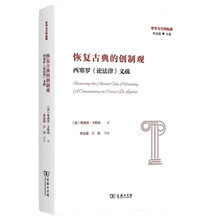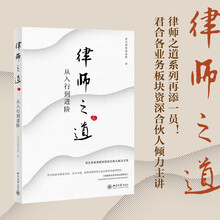第二,目前看到的都是纸上的条文,而少有践行中的实际运作形态情形。纸面上的文字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究竟有多少偏差,需进一步占有材料。
第三,在严酷的军事作战年代,中共中央最主要的精力是在军事作战,地方政权的许多举措只是权宜之计,是服务于军事作战的,而且为了与国民党在政治形象上进行较量,根据地实行了许多不同于今天的制度设计。
因此,缘起可能如福柯、德勒兹等坚持断裂、碎片化意义的观点所否认的那样是学术自负。缘起考究的意义只在于当下,如皮亚杰通过研究儿童心理,来探求人类认知的起源;文化人类学者通过对残存的初民社会的考察,力求发现现代人类文明的问题。但将两个分处于不同时空情境中的历史片段勾连在一起,是需要想象力的,而驰骋的想象力扭曲历史实在,并不完全是一种简单的认知偏差,在利益诉求多样、权力格局多元的形态下,再造历史的目的有时是一种有意识,或虽无意识但却可能落入利益纷争中的非单纯学术活动。
自1993启动《刑事诉讼法》修改就开始的司法体制改革争论,因为涉及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诸机关权力重新调整,已经成为中央核心决策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学术界都关注的问题。而不断地强化、论争自己部门在国家政制结构中的位置,是确保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扩权,至少是不丢权的重要手段,不但寻求支持于学理,而且借力于域外的成例,更要求诸于传统正当性。对司法体制改革,最高决策层的态度是:“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