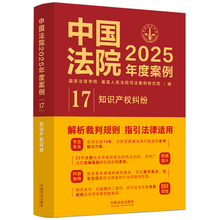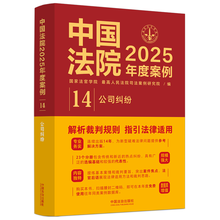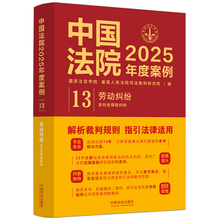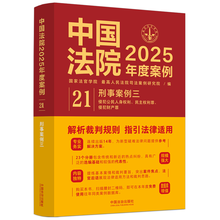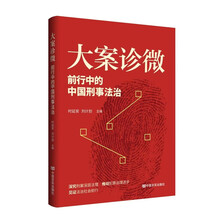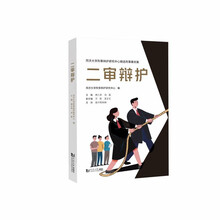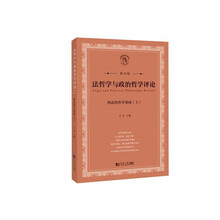第二章着重对本体论法律解释范式进行批判。哲学解释学的前理解、效果历史、诠释学循环、事物的本质、视阈融合、对话以及解释的普遍主义、读者中心论、反对方法等基本概念、特征和原理,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并不符合法律解释的规范性。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并非意味着方法论解释学已被其超越或取代;相反,本体论解释学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标志着其向方法论解释学回归的必然趋势。<br> 第三章考察了赫施与利科对解释学传统范式的坚持、贝蒂对法律解释学方法论的贡献,论证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并非日渐式微;相反,其在当代的信徒或支持者,仍然高举客观性、确定性的旗帜,批评本体论解释学存在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顽疾。法律解释学应“回到经典”、回到方法论范式,坚持在法律文本的意义框架内寻求标准,将维护立法者原意作为其基本诉求。<br> 第四章论证了解释者的主体性取决于作者、文本和读者等多种制约因素的互动。作者的权威性和体制性安排,确保了文本的经典化和读者的信仰面向。文本权威的建立伴随着读者对作者权威的认同。读者在信仰作者和认同文本权威的方式之下去理解、解释和应用,反过来又强化了文本权威以及对作者的信仰。法律解释学应明确反对后现代解释学对法律规范的过度诠释;应借鉴圣经解释学“解经”和“释经”之过程法,坚持传统方法论范式。<br> 第五章主要反思法律解释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范式之争,指出“据法审判”是法治的常态,“不据法审判”只是弥补法治局限性的权宜之计。法律解释学在本质上是附属于法治的一门学问。法律解释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现代性,而不在于后现代性。后现代解释学倡导差异性、创造性、多样性,对于合法性、客观性、明晰性、建设性等现代法律知识属性进行解构,使解释陷入了无穷后退的“囚徒困境”。法律解释学应捍卫现代性的方法论。<br> 第六章通过对施莱尔马赫、萨维尼客观主义解释范式的重新解读,阐释了经典法律解释范式确定性、客观性的认识论基础以及合法性、正当性资源。尽管法律解释方法论自身还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但这并非是无法解决的“解释学困境”。与后现代解释学的“囚徒困境”相比较,我们宁愿选择捍卫现代性的法律解释方法论范式。法律解释学对于司法实践真正能够作出实质性贡献的,就是方法论。<br> 第七章到第十一章分别阐述了经典法律鳃释的各种要素:文义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以及体系解释在现代的延伸——合宪性解释。笔者对各种解释要素的含义进行了详细考察,并阐释其各自独特的方法论功能或价值。文义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及合宪性解释等要素,在解决司法过程中的大部分案件或常规性案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效。<br> 第七章:法律解释的文义要素系指对法律文本语言这个媒介进行解释,以探寻立法者思想与法律意图的一种解释方法。它包含普通含义规则和专门含义规则。文义要素为法律解释结果限定规范意义范围,以此维护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已成为法律适用者进行法律解释时所依凭的最强有力手段之一。所谓的扩张解释或限缩解释,脱离了平义规则,实际上进人了法律续造的地带。<br> 第八章:法律解释的逻辑要素不仅涉及法律文本的合逻辑性,更关涉法律发现过程的合逻辑性这一法律方法论的核心问题。谁也不能否认传统逻辑要素在解决大量简单案件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法律解释中事实与规范对接的复杂现象对逻辑要素的方法论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现代逻辑的不断革新,人们对于法律解释的逻辑要素也有了更加丰富、深刻的认识。霍姆斯的“逻辑一经验”命题曾被视为反逻辑的一面旗帜;然而这是后人无视其所处时代人们对于逻辑与经验关系的狭隘认识,而得出的片面结论。<br> 第九章:法律解释的历史要素系指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之上,阐明对立法产生制约作用的历史规定性,揭示法律中所蕴涵的规范意图。对历史解释要素的理解应该尊重萨维尼的原意,不应把历史解释仅仅和立法史等背景资料相联系;同样,也不应将历史解释方法与对法律文本规范含义的探究割裂开来,并错误地将后者归人所谓(客观)目的解释方法的范畴。历史解释对于限制法官个人专断发挥着特殊功效。清晰的历史规范目的,是法律解释的重要对象与合理界限。<br> 第十章:法律解释的体系要素既关涉内在与外在体系之分,又涉及广义与狭义体系解释之分。它可能意指因同一法律内部的规定之间的或者不同法律部门的规定之间的逻辑与价值关联而产生的解释,也可能意指因法律之间的不同规定发生冲突、包括法律与宪法规定相互冲突时所引发的解释。作为文本论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具有强大的方法论功能,尽管也存在着需要克服的某些局限性。<br> 第十一章:法律解释的合宪性要素系指当法律规范产生多个可能解释时,法官依职权应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并使该规范得以维持的解释。它是基于现代社会强调宪法基本价值而新出现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其实质乃是传统法律方法论的体系解释向公法领域的延伸。司法过程中正确适用合宪性解释方法,需要遵循合宪性推定等原则与规则。合宪性解释方法是目前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条有效路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