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冬长夏短,转眼迎来了第一场冬雪,雪花漫天,乌鲁木齐美术出版社家属院内的平房高低错落,忽然间戴上厚厚的雪帽子。红玉家低矮的小平房就安卧在出版社家属大院的一座四合院内。
一日清晨,唐涛正在准备晚饭,一边劈柴生火,一边咒骂着恶劣的天气。他不讨厌下雪,他厌烦担忧的是落在房顶,堵在门前的积雪,家里可以派上阵的只有六岁的女儿红梅。
唐涛对枯燥琐碎的家务活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一赶上他做家务,他就情不自禁地幻想,哪一天,李钺摇身一变,宛若《聊斋志异》中的美丽狐仙,迈着碎步,心甘情愿地替他烧饭洗衣。遇到沉重的体力活时,他就巴不得红梅变成身强体壮的男孩子。
他想:“都说人多力量大,可家里多一个孩子好像多出一千件家务事。大学毕业那年,自己怀着一颗红心,瞒着母亲搭上一辆列车就来到了新疆。几年过去了,老妈仍然以为我夜里睡帐篷,白天骑大马。请她千里迢迢地前来照管孩子们,到头来会使我落下不孝的罪名。红梅是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帮着拉扯大的。”
唐涛神思不闲,两腿蹲地,右手紧握住一把嵌着木柄的小斧头,不停地劈向左手扶持斜立的一截柴火上,劈裂的柴火如被砍的小人左右前后地扑倒在地,发出“嚓”,“嚓”,“嚓”的声音。“唉,生活啊,生活——”他自言自语,一只脚将已经劈开散落的柴火踢拢成堆,转身在一盛水的搪瓷盆中把手洗净。他跨过屋里的两个门槛后,瞧见李钺烦躁不安地在狭小的卧室内蹀躞。红梅坐在床沿上一会儿摸摸红玉的小脚丫,一会儿捏一捏红玉的圆而多肉的鼻子。
“唐涛,你的耳朵被棉花塞满了,我喊你喊得嗓子都哑了。炉子生着了吗?房子怎么冷得像冰窟,火墙摸起来还是冰的?红玉刚才打了好几个喷嚏。”李钺双眉紧蹙,一见唐涛就扯着嗓门数落他。她身披一件蓝色棉大衣了整个人被厚重的棉衣遮住了三分之二,胸口敞开处露出棉衣里层一绺一绺发黄的羊毛,两只硕大的乳房虽然被挡在灰黑的棉背心后面,却有种喷薄欲出的气象。唐涛扬起眉毛,气鼓鼓地瞪住她:“我不是来了吗,就你性急,同你过日子,脾气再好的人也会被你逼得折寿。我这辈子算是没救了。”说毕,他用手抚摸红玉的额头,转头冲李钺嚷道:“孩子打几个喷嚏,你就一惊一乍的,如果不是你多事,我早把炉子生着了。”他踱到红梅面前,牵住她的手,怜爱地望着她蜡黄清瘦的小脸。
红梅从床沿上跳到地面,仰着小脸朝唐涛撒娇道:“爸爸,我的棉鞋又破了,你让妈给我买双新的,求你了。”李钺立刻高声说:“就数你的鞋子坏得最快,你说实话,是不是又在天天踮起脚尖练芭蕾舞?”红梅朝李钺挤眉弄眼,故意撅起小嘴巴怪声怪气地说:“我就要跳芭蕾,我在喀秋沙奶奶家住的时候,奶奶天天教我跳,她还说,学会芭蕾舞,长大后,我就会成为‘说女’。”“不是说女,是淑女。我家红梅现在像个小淑女。”唐涛笑嘻嘻地说,心里着实喜欢红梅。他拍着胸脯许诺道:“你会得到一双新鞋。”红梅兴奋地旋转身体,摆出一个又一个优美舞姿,看得唐涛心里乐滋滋的,但他想起什么,突然板起脸说:“别跳了,赶快拿上铁锹去门前扫雪,房顶上的雪由我来扫。我得赶紧把火炉生着。”他疾步离开,李钺在他背后略带哭腔地嚷起来:“你会许诺充好人,钱从哪里来?你不管家,不知道我的难处,三年管家人人嫌。我嫁给你有什么好,结婚时都是靠我当姑娘时攒下的钱置办这点家当——”
李钺话音未落,就听见窗外传来“砰”“砰砰”,“砰、砰砰砰”,……一阵枪声。这么密集的枪声,唐涛平生第一次听见,惊骇中本能地从门缝往外觑,除了“砰”,“砰”的枪响,他一无所知。几分钟过去了,邻居们纷纷走出家门,互相打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儿,有消息传来,乌鲁木齐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市一中发生了武斗事件。一时间,美术出版社的家属院里好不热闹,几乎家家挤满了串门的邻居。三三两两的邻居从唐涛家进进出出,小道消息不断翻新。在议论纷纷中,唐涛的铁炉里终于冒出热气,增添了众人的谈兴。
唐涛不时地告诉李钺一些有关死亡和人员受伤的消息,但她听到后显得无动于衷,只是轻轻摇头叹息:“作孽。”唐涛觉得没趣,闲来无事时在日记本上发发诗兴。
一日黄昏,唐涛嘴里念叨着:“大雪后猎人们架着猎鹰,……”正在寻思下一句时,红梅跑来告诉唐涛:“爸爸,妈妈让我告诉你,妹妹发烧了。”“唉,烦死人了——”“红玉发烧了,你快带她去医院吧,啊?你还站着不动,别人唤你去打扑克时,你跑得比谁都快!”李钺的嗓门比平时高出八度。“就你性急,你忘了最近是什么光景?”唐涛一边嘟囔,一边披上军大衣,伸手向李钺要钱。李钺急忙从枕头下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塞进唐涛的大衣口袋里,催促他快去医院。
当晚雪急风吼,地上的雪约有两尺深,寒气逼人。唐涛抱着红玉在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南门医院奔。街上瞧不见一个人影儿。医院离他家有两公里远,平日里跑着去,喘上几口气就到了,那夜,他感觉自己在长征途中跋涉,盼着立刻爬过雪山。眼见着医院的窗户灯影昏黄,唐涛打起精神一个劲地奔到医院门口。一只脚才踏上台阶,就见门口冒出两个汉子,一高一矮,手上各持一条长棍,厉声喝住他:“谁?”“哇,哇,哇——”红玉响亮的哭声划过夜空。唐涛猛然想起医院已经被“三促派”占领了,吓出了一身冷汗,哆嗦着说:“小孩发烧,要找大夫。”话犹未了,“哇,哇,哇——”小孩的哭声一浪高过一浪,前一嗓子娇软细长,后一嗓子响亮有力。唐涛慌忙摇动怀中被棉被包裹着的红玉:“不哭,不哭。”红玉的小嘴很快闭住了。
唐涛正要与那两人说话,这时耳边小孩的哭声绵长不断,不过,声音明显是从台阶下传上来的。一眨眼的功夫,唐涛眼前冒出一个抱着襁褓的男人。那男人比唐涛高出一个头,就连他怀中的襁褓也比唐涛的女儿长出一大截。刚才那响亮的哭声原来是他孩子吼出的。“我儿子发烧,再烧下去,担心脑子被烧坏!”那男人尖声说。
“你们两个站在一起,不许动。”两个手持长棍的汉子绕着两个抱孩子的男人走了一圈,上下打量着他俩。那男人襁褓中的孩子哭声不断,惹得人心烦。唐涛定定神,借着医院里透出的光亮,用眼角的余光看见那男人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你们站在哪一边,三新派还是三促派?”其中一个持棍的矮个汉子凶狠地盘问道。唐涛听到这个问题,好像要去抢金元宝,争先回答道:“我坚决拥护三促派!”身旁的男人也附和着:“站在三促派,站在三促派一边。”唐涛暗自庆幸,多亏晓得三促派的动向,否则答错一句,后果不堪设想。
持棍的高个汉子同矮个汉子小声嘀咕了几句,说得矮个汉子直点头。高个汉子甩着棍子钻进医院里,留下矮个汉子把守大门。矮个汉子朝唐涛眼前一挥手,嘴巴朝医院里努了一努,示意他们可以进门。唐涛迈开步子,哪里有门就往哪里冲:“医生,医生在哪儿?”两个男人最后在一间房子里找到一个男大夫。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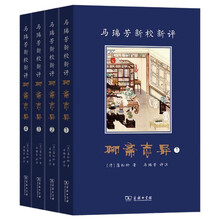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