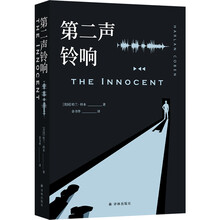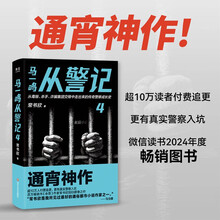第一章 父亲
2000年7月27日午夜时分,北京市玉渊潭公园附近一座写字楼十七层的黄玉生律师事务所一间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事务所的首席合伙人,48岁,身高1.76米,体重93公斤的黄玉生坐在写字台后面的转椅上,像个弥勒佛,斜对面的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他的外甥赵元,赵元身高1.82米,长得非常帅气,尽管如此,这小子看上去却不怎么讨人喜欢。对面的长沙发上坐着的是他的得力助手,个头只有1.70米,又黑又瘦的曹子煌。
黄玉生不是很喜欢这个外甥,这小子虽然勉强在大学混了个文凭,但本质上却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整天梦想着忽然之间会成为大款,或者被一个富家小姐看中,甚至于哪怕有机会被个富婆包养起来,说不定也能就此平步青云。赵元做事情总喜欢投机取巧,所以黄玉生根本就不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给外甥,要不是看在过世的姐姐的份上,他绝对不会容忍这个狗屁不通的家伙在这里丢自己的脸。
从另一方面讲,赵元也因为在舅舅这里不受重视而满腹怨气,可是凭他的本事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所以只好在这里混日子。
曹子煌原名曹世军,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黄玉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帮过他的忙,得知他的底细以后不仅帮他出谋划策躲避警方的追捕,还让他改名换姓在自己的事务所任了一个闲职。
曹子煌知道自己的斤两,也明白在这里做事其实本质上就等于黄玉生白养着他,因此对老总始终怀有强烈的感恩戴德心理。
今天下午黄玉生专程从深圳返回北京和这两个属下进行密谈,是要把一件极其机密的事情托付给他们两个,可是当真面对面坐下来以后,他又犹豫自己这样做是否太轻率了。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很有钱,有的人却终生过着贫穷的日子?”黄玉生一边用指头敲着桌面,一边问两个属下,即使到了现在他也不能确定是否应该把那件事情托付给他们。
“我想,主要的原因在机遇吧。”赵元犹犹豫豫的应到,而曹子煌则有些尴尬的坐在那里没有插话,他从来没有深入想过这类问题。
黄玉生笑着摇了摇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机遇,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
“您的意思……”赵元表面上对舅舅恭恭敬敬,可是内心深处根本就看不起这个自以为是的长辈。
“如果有这样一个机遇摆在你们面前:投入很少的成本,一旦成功就能获得非常丰厚的回报,这样的事情你们愿意做吗?”黄玉生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已经决定要把事情交给两个属下了。
“能丰厚到什么程度?”赵元的眼睛一亮,紧张的看着舅舅,而坐在一边的曹子煌似乎没有提起很大的兴趣。
黄玉生笑了:“多到你不敢想的地步。”
“一百万?……五百万?”
“不要乱猜了,这件事情做起来不但要非常认真,还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可能整个项目要持续几年才能获利成功,我需要头脑清晰,做事稳妥的……”
“舅舅,就交给我好了,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赵元迫不及待地说道。
黄玉生看了看曹子煌,他知道曹子煌不会在乎金钱上的回报,只要他黄玉生一声令下,就算为他杀人,这个人也不会有半点含糊。
“好,我打算让你们两个人负责一个秘密项目,项目运作期间绝对不可以把任何信息泄漏给任何人。另外编制上你们是公关部的人,但是要直接归我指挥,我关照一下公关部经理,没有人会干涉你们的事情。”
“我们要调查什么案子?”赵元把身子往前探了探。
黄玉生看了看猴急的外甥,笑了:“项目启动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你们去找一个人。”
“黄总要找什么人?”一直沉默的曹子煌此刻开了腔,他认为找人的事情他比较在行。
“一个男人,一个三十二岁的男人。”
“这……,范围有点太大了,您能给我们一些资料吗?”
“资料?”黄玉生摇了摇头,“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早就去世了。”
“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入手调查这个人?”曹子煌有些疑惑地问道。
“就从……二十四年前的今天开始吧。”黄玉生看了看两个属下。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赵元问道。
黄玉生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凌晨1点45分。“二十四年前的今天,再过两个小时,中国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1976年7月28目的凌晨3点42分,一道蓝光在唐山的上空闪过,一场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灾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了。几乎就在一瞬间,唐山市区被一场七点八级的强地震夷为一片废墟。
瞬间的灾难使得242419人丧生,36万人受重伤,70万人受轻伤,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数十万居民转眼间就成了失去家园的难民。
几乎就在地震的当天,大规模的救援运动在全国展开了。十几万解放军战士组成的救灾队伍从四面八方赶赴唐山,由于道路被大规模毁坏,多数战士要急行军几十公里才能到达市区。面对这场空前的浩劫,人们在短暂的惊慌、悲哀之后,迅速展开了自救与救援行动。
8月8日,地震过后的第十二天凌晨,初生的太阳从废墟上升起,面对着大自然的这一残酷杰作,郑天豪站在城市的边缘缓慢而绝望地蹲了下来,他甚至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此时此刻,即使往他的衣服里塞进十几条毒蛇也不可能让他感到害怕了。
他的大脑里面仿佛出现了一个漩涡,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念头在里面蹦蹦跳跳,可是他却无法抓住哪怕一点点的实质性内容。
在郑天豪的记忆里,当年被沈威加害的那个时期是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一页,可是如今站在城市的边缘,他竟然觉得被揪斗、被毒打的时刻简直过的是天堂般的日子。
梅在生下儿子的第二天就走了,她是一个干净的人,看不得人间太多的污浊,也看不到一丝生活的希望。自己把儿子送出去以后也想要走,可是儿子却在关键的时刻救了自己。
孩子一出生就显得与众不同,出了娘胎就开始哭,哭得声嘶力竭,谁也哄不好,梅自杀以后,他就不哭了。——莫非他知道母亲就要舍下他而去,想用可怜的哭声留住她吗?当自己把他放到光明电影院石柱后面的时候,他也是一声不吭,可是等那个中年妇女路过的时候,他却忽然大大地哭了一声。郑天豪相信那个女人一定会是一个好的母亲,他坚信儿子的选择不会错。
“八年了,别提他了!”郑天豪学着样板戏里面的叫板,喃喃说了一句,双手无力地抱住了自己的头,眼泪缓缓地流了下来。
八年前,当郑天豪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忍着剧烈的痛楚,躺在铁轨上打算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儿子的笑脸忽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就在列车即将压碎头颅的那一瞬间,他从铁轨上滚了下来。儿子不愿意他死,他不能就这样丢下他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儿子的哭声没有留住母亲,但是做父亲的不能再让他失望了。
不管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他也一定要为了儿子活下来,他不相信中国永远都是沈威之流的天下,黑夜总会过去,自己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坦然回到儿子身边,他会把原本属于儿子的爱加倍还给他,到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能把儿子从他的身边带走了。
当夜,郑天豪爬上北上的货车,历尽千辛万苦,独自一人来到大兴安岭,隐姓埋名,在林区成了一名普通的伐木工人。
如今他回来了,然而没有他想象中的阳光灿烂养育他的城市刚刚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灾难。
儿子能幸免于难吗?郑天豪相信他一定不会有事,如果儿子真的遇难了,自己一定会有感觉的。这孩子一出生似乎就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他曾经要挽留母亲,还救下了父亲,如果当真遇到危难,就算自己远在天涯海角也能感受到儿子的求救信号。——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自己在大兴安岭好像并没有过什么怪异的感觉。
深山里听不到广播,当时也没有卫星电视。7月下旬,大兴安岭下了一场暴雨,进山的公路被冲垮了,林区的给养车在8月3日上山以后才带来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
突如其来的噩耗险些把郑天豪变成呆子,他定了定神,借口有事去县城买东西,便跟着给养车下了山。到了县城,他立刻坐上南下列车来到河北境内。他知道1966年河北邢台曾经发生过一次六点八级的地震,那次地震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七点八级地震应该更强烈一些吧?
接近唐山地区的时候,铁路就断了。他改乘公共汽车走了几十公里,等汽车也不能前进的时候就开始步行。路上,他不断地从似乎深不见底、有时还冒着硫磺气味的裂缝上面跳过,沿途乡村震灾后的断壁残垣以及灾难后沉默寡言的人群都给了他深深的震撼:这里都已经如此了,唐山这个地震中心会被破坏到什么地步?郑天豪浑身发冷,原本还有的一点信心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儿子,你还在人世吗?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忍不住哭了起来。
清冷的阳光下,郑天豪在废墟里踽踽独行,整个城市都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腐烂的气息,甜丝丝地使人欲呕。消防汽车在废墟问临时清理出来的路上缓慢驶过,高压水龙头喷出的消毒水洒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这里或者那里,只要有废墟,就有解放军战士在奋力挖掘。战士们几乎都是凭着双手在废墟上工作,只有在绝对不会伤害到废墟下的群众的时候他们才会动用撬杠一类的简单工具。郑天豪梦游一般地走着,偶尔会听到一声疲惫而嘶哑的欢呼:“叫卫生兵,这人还有救!”
废墟问,这里或那里零散地堆放着装有尸体的黑色塑料袋,货运汽车走走停停,搬运工人就像农民搬动麻袋一样,熟练地把尸体堆放到车上,然后跳上去坐在尸体旁边,汽车开动,再停下,继续装车,娴熟的动作之间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郑天豪战栗着往前行走,不时用指甲掐一下胳膊,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路边的空地上搭建了许多临时帐篷,生还的以及获救的百姓们神情悲伤地在帐篷内外活动,身体好些的则默默地协助解放军战士在废墟上挖掘着。
一个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的女人神情紧张地坐在路边废墟的一角,旁边站着一个解放军战士,那个战士大概只有十八岁,十根手指肿得像胡萝卜一般,上面缠满了脏兮兮的纱布。
“孩子,放我走吧,我不是已经都交代了吗?你们为什么叫执法队?执法队是干什么的?”
老女人的旁边放着十几块各式各样的手表。
小战士有些神色凄然地看着老女人,一言不发。
“你们要枪毙我吗?我只是在死人身上拿了点东西,又不是你们说的打砸抢份子,孩子,放了我吧,我儿子比你还大一些……”
“大娘,我做不了主,您也知道,非常时期必须用非常的手段维护治安。”
“非常手段是什么意思?”老人的神色异常惊惶。
郑天豪地看着这一幕,他隐约觉得那个老女人恐怕要有很大的麻烦了,可是周围的人似乎对此没有半点兴趣,因为刚刚经历了世上最惨烈的灾难,其他任何事情似乎都显得平淡无奇了。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日浩然,沛乎塞苍冥……”
郑天豪一边走着一边喃喃地背诵着文天祥的《正气歌》。
为什么忽然想起这首诗?他悚然一惊,想起了妻子正是从这首诗里面给儿子取的名字。妻子服毒自杀以前,咬破自己的手指,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三个字:郑浩然。
郑天豪由妻子想到了沈威,那个混蛋能躲过这一劫吗?他还是造反派的头目吗?过去的八年,每天他都咬牙切齿地把这个名字偷偷念叨几遍,可如今面对劫难后的城市,他却真诚地希望沈威还活在人世问。
此时此刻如果两个人再次见面,他还会像当初一样对待自己吗?经历了这样的灾难,人世间再大的恩怨似乎也都显得不值一提了。相逢一笑泯恩仇,这话最开始是谁说的?他一定也经历过类似的灾难吧。
可是我真的能原谅沈威吗?除非我的儿子没有事。要知道,当初如果不是他步步紧逼,妻子怎么可能自杀,我又怎么可能抛弃儿子?算了,只要儿子平安无事,我不再怨恨任何人……
郑天豪昏头涨脑地往前走着,心想只要找到那座小楼的位置,一定会见到儿子的。儿子八岁了,他会认我这个爸爸吗?见面以后我该说些什么?他的养父养母愿意我认孩子吗?不,我就随便看看,只要孩子平安,我转身就走。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当然也就没有资格去当人家的父亲了。
“是这里了。”
郑天豪绝望地站在一片瓦砾中间,周围是坍塌的楼房堆成的几座小山。这里曾经是一条小巷,再往前走十几米,往右拐进去一段路就是那座红色的三层小楼。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本来他以为自己会飞也似地奔向目的地,可是就在那座小楼近在咫尺的时候他却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走到那里,虽然不知道结局,可是毕竟还有希望,他害怕永远也等不到儿子的拥抱了。
他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八年前,面对阴险的沈威,他也这样站着,手里握着一枚双面刀片,怀着可怕的决心要和沈威进行一场生死搏斗。
当时,沈威的皮带高高地举了起来,却犹豫着没有立刻落下去。
“你好像不怕我。”沈威狞笑着逼进一步。
“太看得起自己了,你有什么好怕的?”郑天豪昂然笑对沈威。
“好大胆子,敢这样说话!”沈威顿了一顿。
“阿梅被你害死了,我要为她报仇!”
郑天豪狞笑着拿出刀片“嗖”的一声向沈威的颈项划了过去。
沈威似乎惊呆了,然而与其说郑天豪的复仇行为出乎他的预料,不如说是对方向他公布的消息让他感到震惊。微弱的灯光下,一道寒光划着弧形向他挥了过来,沈威本能地闪了一下,左手一抬,轻轻巧巧地握住了郑天豪的手腕。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