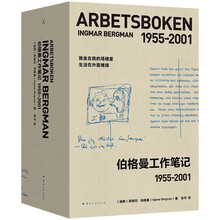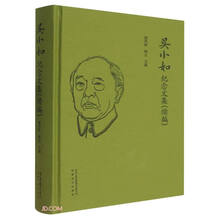滕回生堂的今昔<br> 我六岁左右时害了疳疾,一张脸黄僵僵的,一出门身背后就有人喊“猴子,猴子”。回过头去搜寻时,人家就咧着白牙齿向我发笑。扑拢去打吧,人多得很;装作不曾听见吧,那与本地人的品德不相称。我很羞愧,很生气。家中外祖母听从庸妇、挑水人、卖炭人与隔邻轿行老妇人出主意,于是轮流要我吃热灰里焙过的“偷油婆”、“使君子”,吞雷打枣子木的炭粉,黄纸符烧的灰渣,诸如此类药物。<br> 另外还逼我诱我吃了许多古怪东西。我虽然把这些很稀奇的丹方试了又试,蛔虫成绞成团地排出,病还是不得好,人还是不能够发胖。照习惯说来,凡为一切药物治不好的病,便同“命运”有关。家中有人想起了我的命运,当然不乐观。<br> 关心我命运的父亲,有一天特别请了一个卖卦算命土医生来为我推算流年,想法禳解命根上的灾星。这算命人把我生辰支干排定后,就向我父亲建议:<br> “大人,少爷属双虎,命大,把少爷拜给一个吃四方饭的人做干儿子,每天要他吃习皮革蒸鸡肝,有半年包你病好。病不好,把我回生堂牌子甩了丢到长河潭里去!”<br> 父亲既是个军人,毫不迟疑的回答说:“好,就照你说的办。不用找别人,今天日子好,你留在这里喝酒,我们打了干亲家吧。”<br> 两个爽快单纯的人既同在一处,我的“命运”便被他们派定了。<br> 一个人若不明白我那地方的风俗,对于我父亲的慷慨处会觉得稀奇。其实这算命的当时若说:“大人,把少爷拜寄给城外碉堡旁大冬青树吧。”我父亲还是会照办的。一株树或一片古怪石头,收容三五十个干儿子,照本地风俗习惯,原是件极平常事情。且有人拜寄牛栏的或拜寄井水的,人神同处日子竟过得十分调和,毫无龃龉。<br> 我那干爹除了算命卖卦以外,原来还是个出名草头医生,又是个拳棒家。尖嘴尖脸如猴子,一双黄眼睛炯炯放光,身材虽极矮小,实可谓心雄万夫。他把铺子开设在一城热闹中心的东门桥头上,字号名“滕回生堂”。那长桥两旁一共有二十四间铺子,其中四间正当桥垛墩,比较宽敞,许多年以前,他就占了有垛墩的一间。住处分前后两进,前面是药铺,后面住家。铺子中罗列有穿山甲、羚羊角、马蜂巢、猴头、虎骨、牛黄、狗宝,无一不备。最多的还是那几百种草药,成束成把的草根木皮,堆积如山,一屋中也就长年为草药蒸发的香味所笼罩。<br> 铺子里间房子窗口临河,可以俯瞰河里来去的柴炭船、米船、甘蔗船。河身下游约半里,有了转折,因此迎面对窗便是一座高山,那山头春夏之际作绿色,秋天作黄色,冬天为烟雾包裹时作蓝色,为雪遮盖时只一片炫目白色。屋角隅陈列了各种武器,有青龙偃月刀、齐眉棍、连枷、钉耙。此外还有一个似桶非桶似盆非盆的东西,原来这是我那干爹年轻时节习站功所用的宝贝。他学习拉弓,想把腿脚姿势弄好,每个晚上蜷伏到那木桶里去熬夜。想增加气力,每早从桶中爬出时还得吃一条黄鳝的鲜血。站了木桶两整年,吃了数百条黄鳝,临到应考时,却被一个习武的仇人揭发他身份不明,取消了考试资格。他因此斗气离开了家乡,来到武士荟萃的风凰县卖卜行医。为人既爽直慷慨,且能喝酒划拳,极得人缘,生涯也就不恶。做了医生还舍不得把那个木桶丢开,可想见他还不能对那宝贝忘情。<br> 他家中有个太太,两个儿子,太太大约一年中有半年皆把手从大袖筒缩到衣里去,藏了个小火笼在衣里烘烤,眯着眼坐在药材中,简直是一只大猫。两个儿子大的学习料理铺子,小的上学读书。两老夫妇住在屋顶,两个儿子住在屋下层桥墩上,地方虽不宽绰,那里也用木板夹好,有小窗小门,不透风,光线且异常良好。桥墩尖劈形处,石罅里有一架老葡萄树,得天独厚,每年皆可结许多球葡萄。另外还有一些小瓦盆,种了牛膝、三七、铁钉台、隔山消等等草药。尤其古怪的是一种名为“罂粟”的草花,还是从云南带来的,开着艳丽煜目的红花,花谢后枝头缀了绿色果子,果子里据说就有鸦片烟。当时本县还不会种鸦片烟,烟土全是云南、贵州来的。<br> 当时一城人谁也没见过这种东西,因此常常有人老远跑来参观。当地一个拔贡还做了两首七律诗,赞咏那个稀奇少见的植物,把诗贴到回生堂武器陈列室板壁上。<br> 桥墩离水面高约四丈,下游即为一潭,潭里多鲤鱼鳜鱼。两兄弟把长绳系个钓钩,挂上一片肉,夜里垂放到水中去,第二天拉起就常常可以得一尾大鱼。但我那干爹却不许他们如此钓鱼,以为那么取巧,不是一个男子汉所当为。虽然那么骂儿子,有时把钓来的鱼不问死活依然掷到河里去,有时也会把鱼煎好来款待客人。他常奖励两个儿子过教场去同兵将子弟寻衅打架,大儿子常常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回来时,做父亲的一面为他敷那秘制药粉,一面就说:“不要紧,不要紧,三天就好了。你怎么不照我教你那个方法把那苗子(湘西地方对苗族人的轻蔑称呼)放倒?”说时有点生气了,就在儿子额角上一弹,加上一点惩罚,看他那神气,就可明白站木桶考武秀才被屈,报仇雪耻的意识还存在。<br> 我得了这样一个干爹,我的命运自然也就添了一个注脚,便是“吃药”了。我从他那儿大致尝了一百样以上的草药。假若我此后当真能够长生不老,一定便是那时吃药的结果。我倒应当感谢我那个命运,从一分吃药的经验里,因此分别得出许多草药的味道、性质以及它的形状。且引起了我此后对于辨别草木的兴味。其次是我吃了两年多鸡肝。这一堆药材同鸡肝,很显然的,对于此后我的体质同性情都大有影响。<br> 那桥上有洋广杂货店,有猪牛羊屠户案桌,有炮仗铺与成衣铺,有理发馆,有布号与盐号。我既有机会常常到回生堂去看病,也就可以同一切小铺子发生关系。我很满意那个桥头,那是一个社会的雏形,从那方面我明白了各种行业,认识了各样人物,凸了个大肚子胡须满腮的屠户,站在案桌边,扬起大斧“嚓”的一砍,把肉剁下后随便一称,就猛向人菜篮中掼去,那神气真够神气。平时以为这人一定极其凶横蛮霸,谁知他每天拿了猪脊髓过回生堂来喝酒时,竟是个异常和气的家伙。其余如剃头的、缝衣的,我同他们认识以后,看他们工作,听他们说些故事新闻,也无一不是很有意思。我在那儿真学了不少东西,知道了不少事情。所学所知比从私塾里得来的书本知识当然有趣得多,也有用得多。<br> 那些铺子一到端午时节,就如我写《边城》故事那个情形,河下竞渡龙船,从桥洞下来回过身时,桥上人皆用叉子,挂了小百子边炮悬出吊脚楼,噼噼啪啪的响着。夏天河中涨了水,一看上游流下了一只空船、一匹畜生、一段树木,这些小商人为了好义或好利的原因,必争着很勇敢的从窗口跃下,凫水去追赶那些东西。不管漂流多远,总得把那东西救出。关于救人的事我那干爹总不落人后。<br> 他只想亲手打一只老虎,但得不到机会。他说他会点血(疑为点穴),但从不见他点过谁的血。<br> 民国二十二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我同那座大桥分别将近十八年,我又回到了那个桥头了。这是我的故乡,我的学校,试想想,我当时心中怎样激动!离城二十里外我就见着了那条小河,傍着小河溯流而上,沿河绵亘数里的竹林,发蓝垒翠的山峰,白白阳光下造纸坊与制糖坊,水磨与水车,这些东西使我感动得真厉害!后来在一个石头碉堡下,我还看到一个穿号褂的团丁,送了个头裹白孝布的青年妇人过身。那黑脸小嘴高鼻梁青年妇人,使我想起我写的《凤子》故事中角色。她没有开口唱歌,然而一看却知道这妇人的灵魂是用歌声喂养长大的。我已来到我故事中的空气里了,我有点发痴,环境空气我似乎十分熟悉,事实上一切都已十分陌生。<br> 见大桥时约在下午两点左右,正是市面顶热闹时节。我从一群苗人一群乡下人中挤上了大桥,各处搜寻没有发现“滕回生堂”的牌号。回转家中我并不提起这件事。第二天一早,我得了出门的机会,就又跑到桥上去,排家注意,在桥头南端,被我发现了一家小铺子。铺子中堆满了各样杂货,货物中坐定了一个瘦小如猴,干瘪瘪的中年人。从那双眯得极细的小眼睛,我记起了我那个干妈。这不是我那干哥哥是谁?<br> 我冲近他摊子边时,那人就说,“唉,你要什么?”<br> “我要问你一个人,一件事,你是不是松林?”<br> 里间孩子哭起来了,顺眼望去,杂货堆里那个圆形大木桶里面,正睡了一对大小相等仿佛孪生的孩子。我万想不到圆木桶还有这种用处。我话也说不出来了。<br> 但到后我告给他我是谁,他把小眼睁愣着瞅了我许久,一切弄明白后,便慌张得只是搓手撂舌头,赶忙让我坐到一捆麻上去。<br> “是你!是茂林!”“茂林”是干爹给我起的名字。<br> 我说:“大哥,正是我!我回来了!老人家呢?”<br> “五年前早过世了!”<br> “嫂嫂呢?”<br> “六月里过去了!剩下两只小狗。”<br> “保林二哥呢?”<br> “他在辰州你不见到他?他做了王村禁烟局长,有出息,讨了个乖巧屋里人,乡下买得七十亩田,做员外!”<br> 我各处一看,卦桌不见了,横招不见了,触目全是草药,“你不算命了吗?”<br> “命在这个人手上”,他说时翘起一个大拇指,“这里人已没有命可算!”<br> “你不卖药了吗?”<br> “城里有四个官药铺,三个洋药铺。苗人都进了城,卖草药人多得很,生意不好做!”<br> 他虽说不卖药了,小屋子里其实还有许多成束成捆的草药。而且恰好这时就有个兵士来买“一点白”。把药找出给人后,他只捏着那两枚一百的铜元,同我呆呆地笑。大约来买药的也不多了,我来此给他开了一个利市。<br> 他一面茫然的这样那样数着老话,一面还尽瞅着我。忽然发问:<br> “你从北平来南京来?”<br> “我在北平做事!”<br> “做什么事?在中央,在宣统皇帝手下?”<br> 我就告他既不在中央,也不是宣统手下。他只做成相信不过的神气,点着头,且极力退避到屋角隅去,俨然为了安全非如此不成。他心中一定有一个新名词作祟,“你可是个共产党?”他想问却不敢开口,他怕事。他只轻轻的自言自语说:“城里前年杀了两个,一刀一个。那个韩安世是韩老丙儿子。”<br> 有人来购买烟签,他便指点人到对面铺子去买。我问他这桥上铺子为什么都改成了住家户。他就告我,这桥上一共有十家烟馆,十家烟馆里还有三家可以买黄吗啡。此外又还有五家卖烟具的杂货铺。<br> 一出铺子到城边时,我就碰着一个烟帮过身,两连护送兵各背了本地制最新半自动步枪,人马成一个长长队伍,共约三百二十余担黑货,全是从贵州来的。<br> 我原本预备第二天过河边为这长桥摄一个影,留个纪念,一看到桥墩,想起十七年前那钵罂粟花,且同时想起目前那十家烟馆五家烟具店,这桥头的今昔情形,把我照相的勇气同兴味全失去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