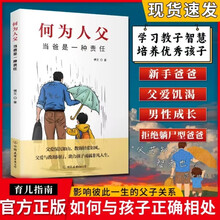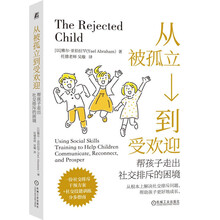第1章 儿童的生活调查
既然婴儿是人,我们就应该时刻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我们必须关注他们如何以一种英雄般的勇气来实现对生命的渴望。
许多人要求我继续研究儿童教育法,这样他们能把我的教育法应用于七岁以上年龄的儿童,这说明他们还在怀疑这一教育法是否完全可行。
他们提出的质疑主要是道德秩序方面的问题。难道儿童不应该现在就开始首先尊重他人的意愿?难道儿童就不应该有那么一天会鼓足勇气去完成一项必须由他来完成的、又确实需要他付出努力的非选择性工作?而且,既然一个人的生活不会总那么轻松自在,不会总那么享受,难道他就不应该学会自我牺牲?
现在的初等教育从六岁就开始导入,七岁时正式实施,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就提出了他们的质疑——现在我们面对的是那些让孩子的感到枯燥无味的数学表和用语法严格约束的枯燥的脑力练习,你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你是要全部取消,还是承认这一切是必须的,孩子们必须学习这些课程?
显而易见,整个争论都围绕着对“自由”一词的解释,而这个词是我所提倡的整个教育体系不可动摇的基础。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所有这些反对声都会被付之一笑。也许那时再出版我这本书,大家会要求我把这些争议连同我的辩论一起从书中删除掉。但是现在,这些还有理由存在,也有必要对这些争议进行讨论。因为即使是人人都坚信的问题也同样会引发争议,所以要给出一个直接、清晰、有说服力的答案确实很难。
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或许能省去我们许多口舌。在卫生学的指导下,在对待婴儿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已经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前是如何对待婴儿的?毫无疑问,许多人还能记得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习惯做法:一定要把婴儿捆起来,否则孩子的腿将来就会不直;一定要把婴儿的舌下韧带剪开一些,以保证孩子将来能说话清楚;一定给婴儿带上帽子,以防孩子将来长成扇风耳;婴儿躺着时一定要时刻密切注意孩子的头部姿势,以保证他的后脑颅骨不会变得过于突出;细心的母亲会经常捋、捏婴儿的小鼻子,好让孩子的鼻子长得鼻梁笔直,鼻头尖尖,而不是鼻梁塌陷,而且鼻头又扁又圆;婴儿出生后不久,她们还会给孩子的耳朵刺洞,带上金耳环,以“改善孩子的视力”。这些习惯在有些国家可能已经遗弃不用了,但还有一些国家仍沿用至今。
有谁会不记得那些各种各样帮助孩子学走路的工具呢?孩子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甚至连神经系统都没发育完全,对他们来说不可能协调其身体各部位做动作,而在这个时候那些妈妈们每天就会花上几小时“教宝宝学走路”。她们用双手托住宝宝的腋下,看着小脚丫毫无目的地来回移动,就自欺欺人地相信宝宝已经开始在学习走路了;又因为孩子的脚弓确实在逐渐形成,而且双脚的摆动也越来越大胆,妈妈们就把宝宝的进步归功于自己每天的教导。终于,当这种运动建立起来的时候——尽管还没有获得平衡感,还不能双脚站立——妈妈们便用带子一类的东西提着孩子的身体,牵引着孩子在地上行走;再不然,如果她们很忙,没有空闲的时候,她们就会把婴儿放进一种铃铛状的篮子里,这种篮子底部宽大,可以防止篮子翻倒;她们把婴儿放在里面,双臂放在篮子外面,宝宝的身体由篮子的上口支撑着;这样虽然宝宝不能用双脚真正站立,却能向前移动,似乎这就是在行走了。
还有一种东西人们刚刚放弃不用,那就是给刚刚学会站立的宝宝戴一种类似凸起的皇冠帽子。这类似于跛子的拐杖:已经习惯于篮子的宝宝,突然失去了篮子的支撑,必定会时常摔倒,这个王冠一样的帽子就可以保护宝宝的头部不受到磕碰和撞伤。
当科学延伸到拯救儿童的范畴时,它又说明了什么呢?科学当然不会提供使鼻梁更直、耳朵不会是扇风耳的绝好方法,也不会提供给妈妈们更好的在宝宝刚出生就立刻能教孩子走路的方法以让妈妈们更轻松一些。不,绝对不会!这首先说明了一个人的头、鼻子和耳朵的形状是天生的;说明了一个人的舌下韧带不断开也能说话;此外还说明腿会自然长直,随着宝宝长大,自然而然就会行走,而不需要人为干预。
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顺其自然,宝宝越是自由地生长发育,他的身体比例就越适合,发育就越迅速,各项功能就越健全。因此我们建议摒弃给婴儿捆襁褓,取而代之以“在自由姿势下最大限度地放松”。也就是说让婴儿的腿完全自由,这会使宝宝躺着时能完全舒展,而不会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宝宝的腿上下乱动是他们在靠这种东西“愉悦”自己。切不要拔苗助长,等时候一到,宝宝自然就会行走的。
现在几乎所有妈妈们都相信这些了,那些卖绑襁褓带子和拉吊孩子走路的带子、还有放置婴儿篮子的小商贩们都确确实实无影无踪了。
结果,宝宝们的腿比以前长得更直,走路也比以前更好、更早了。
这是既定事实,也令人欣慰。因为过去人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腿长的直不直,鼻子、耳朵和头的形状长得漂不漂亮都是我们护理得好不好的直接结果,我们曾为此多么忧心忡忡啊!这是多大的责任,以至于每个人都感到难以胜任!而现在,我们可以放松地说:“这些都是天生的,我会让我的宝宝自由地生长,看着他健康美丽地成长;我要做的只是做一名大自然创造出来的奇迹的安静的旁观者。”
孩子的内心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曾为这些忧虑所困扰:形成性格、发展智力、对情感的表露和调整,所有这些都非常必要,但我们还要自问一下如何才能做到这些。我们或者可以随时随地与孩子的心灵相通,或者用特殊的方式束缚他们,就像过去许多妈妈们做的那样:用手捋捏宝宝的鼻子,用帽子固定宝宝的耳朵。另外,我们把忧虑隐藏于某种很平凡普通的成功之下。事实上,人类的成长中就包括有性格、智力和情感的成长发育。但当缺乏所有这些时,我们就崩溃了。那时,我们需要怎样做呢?谁愿意把性格给一位智力退化了的人、把知识教给一位白痴、把人类情感给一位精神病患者呢?
如果人类获得所有这些品质都确实是靠对心灵控制的方法获得的,那么在孩子们的心灵还很幼小时施加一点点的力量就足够了。但这事实上是不够的。
我们不是精神的谤造者,也不是物质的创造者。是大自然,这个“造物主”把万事万物掌管得有条不紊。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承认“不为自然发展设置障碍”这条原则。我们不能孤立地去处理一个个的问题——例如,什么方法最有助于发展个性、智力和情感?——因为仅仅这么一个问题,就可以揭示出教育的基础:即我们该如何给孩子以自由?
既然我们需要给孩子们这种自由,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些相类似的原则,这些原则类似于已由科学验证得出的、在人体生长发育过程中与身体的成长和各种功能健全相符合的原则;在这种自由中,孩子的头、鼻子和耳朵将达到最完美,其步态也会以其个体的先天能力达到最为完美。这样,也只有这种自由的方式将会引领一个人的性格、智力和情感最大限度地发育完善;也将会引领我们这些教育家的思想,使我们减少争论,使我们更有可能只去安静地看着他们成长,看着大自然创造的奇迹。
这种自由将会把我们从虚构的责任和危险的错误观念所带来的沉重负荷中进一步解放出来。
我们的悲哀在于,我们信以为真地认为我们要为一些与我们根本无关的事情负责,还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正在努力使一些事更加完美,而这些事根本不需要依靠我们就可以独立地自我完善!为此,我们就像傻子一样!而且进一步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使命、真正的责任?如果我们是在欺骗我们自己,那事实又是怎样的?我们哪些行为是有罪的?我们又忽略过哪些应该是有罪的行为?如果我们就像公鸡一样,相信太阳在早晨升起是因为公鸡打鸣,那么当我们头脑理智时我们该知道有什么责任呢?如果因为我们自己忘记了去吃“面包”,那谁会真正挨饿呢?
婴儿“身体救赎”的历史过程对我们来说富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卫生学并没有被限制在论证人体解剖学的范围内,例如它不仅被公众所了解,而且还使所有人都确信身体的发育是本能的。因为事实上,婴儿的健康幸福与体形是否完美没什么关系,真正与之有关的、需要科学干预的是令人吃惊的婴儿死亡率。
当然,现如今考虑这些事情似乎有点匪夷所思,即使在这个婴儿疾病是最大威胁的时期,人们却几乎没怎么像关注婴儿鼻子的形状好看不好看、腿长得直不直那样去关注婴儿的死亡率,而真正的问题——生与死的问题——却被人忽视了。肯定有许多人,比如我自己就听到过下面这样的对话:“我在护理孩子方面经验丰富,我自己就有九个孩子。”“现在有几个孩子还活着?”“两个。”然而这样的母亲竟被看做是权威!
死亡统计所披露出的婴儿死亡率如此之高,我们甚至可以称这种现象为“滥杀无辜”了。这个著名的莱克希斯(Alexandra的昵称,原意是“人类的守护神”)曲线图用于许多国家,说明了人类平均死亡率的问题,从这个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可怕的婴儿死亡问题在整个人类中普遍存在。这应归结为两点不同的因素:毫无疑问,首先一个原因是因为婴儿特有的脆弱;另一个是因为人们缺乏对这种脆弱的保护,而且这种缺乏保护普遍存在。人们不缺乏对婴儿的良好祝愿,父母不缺乏对婴儿的爱,但错误在于无知,在于人们对极大的危险根本没有保护意识。现在对婴儿的生命最有杀伤力的疾病是传染病,尤其是源于肠道的传染病,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问题。在纤弱的身体组织对肠道紊乱非常敏感的这个年龄阶段,紊乱会阻碍营养的吸收,同时产生毒素,这几乎是所有婴儿死亡的元凶。而这些疾病常常由于护理孩子的人习惯性的错误行为而加重。这些错误主要是由于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这种习惯的缺乏会让我们现代人感到震惊,襁褓下僵硬的尿布在阳光下一次次晒干,根本不洗就直接给宝宝换上。其次是对婴儿的喂养没有形成规律。尽管宝宝的口腔内残留物发酵,很明显是要引起口腔炎症了,但是妈妈在哺乳前还是没注意应该清洗一下乳房,清洗一下宝宝的口腔。给宝宝喂奶也毫无规律,宝宝的哭声就是喂奶时间到了的唯一命令,而且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是如此;宝宝越是消化不良或是因此而痛苦,喂食越是频繁,由此宝宝的病痛也就持续加重。过去有谁没见过妈妈为了让宝宝安静下来,把因发烧而小脸通红的宝宝抱在怀里,硬把奶头塞到号啕大哭的小嘴里呢?那些妈妈们也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和做母亲的烦恼!
科学做出了一些规定,要求尽可能讲卫生。它阐述的原则不言而喻,如果有人竟然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为他们制定的,那真是让人瞠目结舌了。这个原则是:即使是最小的婴儿,也要像我们一样有规律地进食,也应该是在消化完前一次的食物之后再吃一些新鲜的食物。因此应该根据宝宝的年龄和其正在发育的身体功能调节状况,制定每隔几个小时喂食一次。不能让婴儿唆食面包干,有些母亲经常这样做,尤其是那些有些消化不良的宝宝,妈妈们为了阻止他们啼哭,就喂他们一些面包干。因为宝宝会把面包颗粒吞下,而他们还没有能力消化这些面包颗粒。
母亲们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忧虑:宝宝哭闹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然而她们这样做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孩子的哭闹少多了,或者完全不哭了;她们甚至会看到仅一个星期大的宝宝在两个小时的喂食间歇期间安安静静,脸蛋红润有光泽,睁着大大的眼睛,他们是那么安静,以至于没有发出丝毫的生命迹象,就像是大自然在一刹那间庄严地静止不动了。宝宝们为什么会不断哭闹呢?那些哭闹实际上就是信号,表明的意思是:痛苦和死亡。
世界对这样哭嚎的小生命什么都没有做,他们被裹在襁褓中,而且经常是由一个没责任能力的孩子照看,宝宝们没有自己的房间,没有自己的床位。
是科学拯救了他们,给他们创造出了保育室、摇篮、婴儿室、适合他们穿的衣服,还有一些大企业和医学专家为他们专门制作的用于断奶后的卫生食品和专用营养品。总之,是科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清新、睿智、充满欢乐。婴儿成为有自己生存权利的新人,从而引出了一个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新领域。其结果就是婴儿卫生法则被普遍推广,了解这一点的人数相应的直线上升,从而使婴儿死亡率也相应地下降了。
由此可见,因为有创造力的大自然能比我们更好地塑造婴儿的精神,所以当我们说婴儿也应该一样有精神自由时,我们并不是说就要放弃或忽视孩子的精神问题。
也许我们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就会明白,虽然我们不能直接雕琢孩子的个性、智力和情感,但是或多或少我们忽视了一些责任和本该担忧的事情,而精神的“生与死”正依赖于这些责任和应该被我们忧虑的事情。
因此,自由原则并非放弃原则,而是那种把我们从幻想拉回现实,引导我们进行最为主动高效的护理孩子的原则。
儿童现在的自由完全是身体的自由
卫生学已经给婴儿的物质生活带来了解放,如不再用襁褓包裹宝宝、婴儿也能有户外生活、婴儿的睡眠不再受人为干预可以一直睡到自然醒等,这些事实都是最有力、最明显的证据。但这些仅仅是获得解放的手段,而获得自由更为重要的措施是在婴儿生命旅程的最开始便排除那些疾病和死亡的最大威胁。只要某些最基本的错误得以纠正、将阻碍婴儿生命得以延续的障碍扫除,不仅婴儿的成活率会大幅度提高,而且婴儿的生长发育也将得到明显的改善。那么确实是卫生学帮助他们在体重、外表形象、漂亮程度、身体发育等方面有所改善和提高吗?答案是:卫生学并没有做到所有这些事情。就像福音书上所说:谁能只通过思考就能使自己的形象更高大呢?卫生学仅仅排除了妨碍孩子生长发育的障碍,这些外部限制抑制了身体的自然发育和生命的一切自然进化,而卫生学冲破了这些枷锁的束缚。因此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种自由所起的作用,每个人都鉴于这种事实一再地坚持这种观点:孩子应该拥有自由。由于“被满足的儿童物质生活的条件”与“已获得的自由”之间的直接关系,现在已得到了普遍而直观的共识,因此人们养育婴儿就如同呵护幼小的树苗一般。现如今的孩子享受着远古时代种植园里被精心照料的蔬菜般的呵护:上好的肥料、充足的氧气、适宜的温度、对消灭能引起蔬菜疾病的寄生虫的细心等。是的,我们因此可以说,对这些小皇帝的照料就如同别墅里最美丽的玫瑰花一样得到了精心的照料。
把儿童比喻为花朵,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尽管这只是一些比较幸运孩子的特权。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观念。因为婴儿就是人,能满足一株植物的条件不可能满足一个人。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这样说一个瘫痪在床的人:“他只是个植物,而作为人,他已经死了。”如果他听了这话,会有多颓丧,这种悲哀有多痛苦!因为他除了一副人的躯壳,什么都不存在了。
既然婴儿是人,我们就应该时刻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我们必须关注他们如何以一种英雄般的勇气来实现对生命的渴望。
那么儿童的权利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把儿童当作一个社会阶层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把他们当作是劳动者阶层,因为事实上他们确实是在劳动、在创造人类,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他们承受着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磨砺,继续着他们的妈妈做了几个月的工作,但接下来他们的工作更艰辛、更复杂、更困难。刚出生时他们除了有潜力,其余一无所有。甚至成年人都承认,儿童被迫在这个充满了艰难困苦的世界上做每一件事。那么在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里,我们如何去帮助这些生命脆弱的朝圣者呢?他们的降生甚至比动物还要脆弱,还要无助,因为几年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得不适应这样一个由无数代人经过艰苦努力而建成、高度复杂、极其有组织的社会。那么在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当生活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某些权利之上——这些权利要靠积极努力地争取才能得来,要靠法律赋予——既没有任何力量,又没有任何思想的婴儿来到我们中间时,他有些什么权利呢?如漂流在尼罗河上躺在蒲草做成的箱子里的婴儿摩西,他代表着犹太人的未来,但偶尔路过的某位公主就一定会看到他吗?①
我们把机会、运气、偏爱,把所有这些都给了这个孩子。而似乎《圣经》中对埃及暴君的惩罚、对埃及人所有家庭中第一胎死亡的惩罚②永远都要延续下去。
让我们来看一看,当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社会公正是怎样接纳他们的。我们生活在20世纪,而在这个时代,许多所谓的文明国家里,孤儿院是人们公认的慈善机构,奶妈也是社会公认的人群。什么是孤儿院?那其实就是一个关押所,一所黑暗可怕的监狱。在这所监狱里,犯人死去习以为常,就像是中世纪地牢中的人一样,无声无息地就消失不见了,丝毫不留痕迹。这些人从没有被任何人关爱过,他们的姓名被删去,财产被没收。最年长的犯人有可能还对他们的妈妈有些记忆,知道自己有过名字,与那些靠回忆去记忆色彩的美丽和太阳的绚烂的后天成为盲人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或许还能依靠回忆获得一些安慰。但是弃婴则和天生的盲人一样,每位囚犯都拥有比他更多的权利,然而谁更清白无辜呢?即使是在最暴政的年代,那些被压迫的人们也会点燃正义的火炬,最终导致大革命的爆发。那些因为碰巧见证了暴君罪行的人被关入了大牢,还有那些因被关入黑暗大牢而遭受闻所未闻的折磨因此失去了欢乐的人们,他们至少能唤醒人们去争取平等公正的法律制度。但是谁会为那些弃婴放声疾呼呢? 这个社会就不认为他们也是人,实际上他们仅仅是人类的“陪衬”,而又有哪个社会不是用牺牲“陪衬”来保存名节、获得好名声的呢?
奶妈是一种社会习俗,一方面这是一种奢侈的习俗。还在前不久的时候,有一位出身甚至还谈不上是中上阶层的姑娘,在即将结婚时,以其未来夫君答应她的舒适居家条件引以为豪,她提出的条件是:“我要有一个厨师、一个女管家、一个奶妈。”另一方面,刚刚生了孩子的健壮农村女孩看着自己丰硕的乳房,会很得意地想到:“现在我可以找个富裕人家去当奶妈了。”只是在最近,卫生学才呼吁那些因懒惰而拒绝给自己孩子用母乳喂养的妈妈们的行为是可耻行为;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坚持自己母乳喂养孩子的女王和王后们仍然被引证为其他母亲们的学习榜样。卫生学建议把喂养自己的孩子作为母亲的责任是根据一条生理原理做出的:母亲的乳汁比任何东西都更滋养婴儿。尽管这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但是这项职责远没有被普遍履行。走在路上时,我们还能经常看到一位健壮的母亲身边跟随着一位抱着宝宝的奶妈,奶妈也穿红戴绿,衣服上绣着金丝银线,极为得意。有钱人家的主妇不会带衣着不整的奶妈外出的,她们总是带着时髦奶妈,这些时髦奶妈是婴儿卫生方面的专家,他们把孩子像“花”一样精心照料。
那么其他的孩子怎么样呢?如果某些婴儿一个人就有两个母亲给他喂奶,那么另外一个孩子就不会有奶喝了。但问题是母乳不是人工制造的产品,它是大自然的精心分配,即每一个新生命都会分配到相等的一份。只有制造生命才能产生母乳,养牛人对此再明白不过了:他们以非常卫生的方式饲养好奶牛,而把小牛送去屠宰场。每次把那些幼小的生命与他们的妈妈分开时女主人是什么感受!小狗小猫不也是如此吗?当家里的宠物狗生出太多的小狗而喂不起奶,主人只能清除掉一些小狗的时候,女主人心底里也会感到伤心!而这个女主人的宝宝却还由一位身体健壮的奶妈喂奶呢!让女主人伤心的是那只非常想养育自己的狗宝宝而低声呜咽的狗妈妈,它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喂养那么多柔弱的小狗,却还不想失去任何一个。奶妈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她是自愿出卖自己的奶。而那个孩子——她自己的孩子——怎么办,没人关心,甚至连她都不关心。
只有清楚地以法律的形式界定出宝宝的权利才能保护宝宝,因为这个社会是法制社会。没错,这些权利就是财产,绝对的财产;即使你是因为感到饥饿偷一片面包都要被判定为是小偷,你将为此而被法律惩罚,被社会定为叛逆者。而财产权利则构成了社会基础最不可侵犯的组成部分。一位地产管理者把本不属于他的财产卖掉,用换来的钱去享乐,直接导致了财产的真正主人陷入贫困,这种犯罪令人难以想象,因为有谁会去购买没有主人签字的房产呢?而社会构成就是如此。如果有人确实犯下某些罪行,这个人不仅会被判罪,但事实是这些罪行几乎不可能发生。然而对于那些婴幼儿,犯罪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且竟然没人认为这是在犯罪,而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对于孩子来说,有什么能比拥有母亲的奶水更为神圣的呢?孩子可能会用拿破仑大帝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上帝赐予我的。”毫无疑问,他的要求是合法的,而且这是他唯一与生俱来的、只为他而生的资产。他所有的财富就在于:生命的力量、生长的力量、获得活力的力量都来源于乳汁的营养。如果那些没有喝过母乳的婴儿长大后因贫困去艰苦劳作,他们就会身体虚弱、患佝偻病,结果会怎么样呢?多少伤痛、多少意外事故造成的永久性伤残都是因为此病。等将来孩子长大成人了,某一天在工作中出现意外事故并受伤,而且是永久性的时,那么他会在社会道德的法庭上对这个问题导致的结果提出怎样的控诉呢!
在一些文明的国家里,生活富裕的母亲们已经了解到了应该给自己的孩子哺乳,这是因为卫生学家们已经证明母乳喂养对宝宝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利,而不是因为她们已经认识到享受母乳是婴儿的“民事权利”。她们认为那些还保留使用奶妈习俗的国家不如她们的国家发达,但文明程度却相差无几。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妈妈有病不能哺乳孩子又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宝宝是很不幸的。那为什么还要让另一个孩子因为这个宝宝的不幸而不幸呢?无论一个人有多贫穷,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剥夺别人急需的财富。如果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有某位要人需要靠浸泡在人血中才能治愈某种可怕的疾病,那他也不能因为这个目的,就像过去野蛮的皇帝那样让健康人为他流血。这些就是构成我们文明的因素,而文明又把我们与海盗和食人者区别开来,并公认每个成年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但婴儿的权利并没有得到认可。这个事实表明的基本含义是:我们确实认识到了成年人的权利,但没有认识到儿童的那些权利!我们确实意识到了公正的问题,但这只限于那些可以自我保护、自我防卫的人,而对于其他人我们则保留我们的野蛮。因为现在很多民族已经或多或少地从卫生的角度提高了自己,但无论是什么民族,他们同属于一个文明——建立在最强大权利基础上的文明。
当我们开始严肃地审查孩子的道德教育问题时,我们应该先看看我们周围,先调查一下我们为孩子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环境,难道我们愿意孩子们像我们一样,粗暴野蛮地对待弱者吗?难道我们愿意他们像我们一样根深蒂固地认为,对那些不能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就应该独断专行吗?难道我们愿意他们像我们一样,与和我们一样的人交往时是半个文明人,而与那些无知和受压迫的人交往时就是半个野蛮人吗?
如果我们不愿意他们这样,那在我们给他们讲道德教育前,先要模仿那些马上要做教化的传教士们:他们在给别人讲道之前先低下头来忏悔,向教徒们坦白自己所犯之罪。
被剥夺了权利的孩子就像是脱了臼的手臂,只有当脱臼部位复位后人性才能在道德的进化方面起作用,也才能终止附带的因肌肉受损而造成的疼痛和功能失效, 还有终止女人因此造成的痛苦与麻木。儿童的社会问题很明显更加复杂、更加深奥;这不仅是我们眼前的问题,也同样是我们将来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是从心底里认为我们的这种行径是不公正的,就更不用说承认这些就是犯罪了。那么当我们和孩子相处时,他们还有什么粗暴行为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呢?
如何接纳刚刚降临于世的新生儿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周围,只是到了最近我们才开始对接受这么尊贵的客人有所准备。儿童床才发明不久;在数不清的、一味重复的、数量过多、过于奢侈的各类商品中,我们来看看有几样是专门为孩子制造的。没有适合孩子使用的盥洗盆,没有适合他们坐的沙发,没有他们用的桌子、刷子。每个家庭都有许多房间,但没有一个房间是给他们的,是为他们的生活而准备的,只有那些富裕有钱人家的孩子或幸运的孩子才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才有一个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自由放任的地方。
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会遭受多大的痛苦。
假设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绿巨人之中,与我们相比,这些巨人的腿无比的长,身体无比巨大,而且运动起来不知道比我们快多少倍,他们非常灵活,非常聪明。我们想走进他们的房子,可是每个台阶都竟然和我们的膝盖一样高;我们想爬进去,但不得不靠这些房子的主人的帮助;我们想坐下来,但是每个坐椅竟然都和我们的肩头一样高;我们想爬上去坐下,最终还是不得不让他们把我们放上去。我们想清洁一下我们的衣服,但是每一个刷子都非常大,我们既握不住又拿不起它;我们想刷刷我们的指甲,递给我们的刷子就像衣服刷子那样大。我们可能会很想找个洗澡盆来洗个热水澡,但是他们的澡盆都巨大,我们无法将之端起。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绿巨人是一直盼望我们的到来,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他们没有做好接待我们的准备,或是没有做好使我们在他们中间愉快生活的准备。孩子发现他自己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是以玩具的形式存在的,都是为玩具娃娃准备的;丰富多彩、各类极具吸引力的环境条件并没有为他们创设出来,而玩具娃娃却有房子、起居室、厨房、衣柜;成年人拥有的一切都以缩小的形式为他们制造出来,然而孩子们却不能在这缩小了的东西里生活,只能用这些东西自娱自乐。世界和孩子开了个玩笑,因为没人认为孩子是活生生的人。孩子们最终将发现这个社会不承认他们的到来是有价值的。
众所周知,儿童损坏玩具,特别是损坏那些专门为他们制造的东西的这种行为,被视为他们智力发育的佐证。我们说:“他把玩具弄坏是为了弄清楚‘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实际上他是想看看玩具内部是不是还有使他感兴趣的东西,因为他对玩具的外表一点兴趣都没有,有时他粗鲁地打碎玩具,就像一个愤怒的敌人。然而,按照我们的想法,他破坏玩具只是因为顽皮。
借助于周围的事物生存是儿童的自然倾向。他愿意用自己的脸盆,愿意自己穿衣服,愿意真正给一个活生生的人梳头,愿意自己动手扫地,等等;他也愿意有自己的座位、饭桌、沙发、晒衣夹和碗柜。总之,他渴望的就是自己动手做一些有目的的事情,使他自己的生活舒适安逸。他不仅要“行为方面像个成年人”,而且要“具备成年人的全部”,这是他天性和使命的主导趋势。
我们在“儿童之家”里见到过这样的孩子,他像大多数训练有素的工人一样,也像大多数一丝不苟的管理者一样,愉快、耐心、动作舒缓而细致。再小的小事也能让他心满意足:把衣服挂在墙上钉得很矮、伸手可及的挂钩上;把一扇很轻便的门打开,门把手的大小正好适合他的小手;把一把椅子放到某个地方,椅子的重量对他来说并不很沉,他搬动椅子时既不会弄出很大声响,动作又很优雅。因此我们建议:给孩子创造一个每样东西的大小都与他相称的环境,并让他生活在这个环境中。这样有助于发展孩子内在的“积极生活”,而这种“积极生活”可以使孩子有很大成就感,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不仅看到了愉快的简单容易的劳作,而且还看到了精神生活。在这样的和谐氛围中,我们看到,孩子们的每项生活都需要开动脑筋,就像一棵植根于土壤中的种子,正在以唯一的一种方式生长发育:长时间地反复练习。
我们看到,孩子们在生活过程中,虽然专心于自己的工作,但他们的动作很慢,很蹩脚。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就像他们走路很慢,因为他们的腿还没有长长,我们凭直觉感觉到生命正在他们体内逐步完善,就像蛹慢慢地在茧袋里成为蝴蝶。妨碍他们的活动就像用暴力摧残他们的生命。但是你经常如何对待你的孩子呢?我们所有的人打扰孩子时既不感到内疚,又丝毫不加考虑,就像主人对待没有人权的奴隶一样。对许多人来说如果要是对待他们像对待成年人一样表示出“尊重”那是非常滑稽的事情,然而我们却非常苛刻地命令孩子们不要妨碍我们!如果孩子们要做点什么事情,例如自己动手吃点东西,大人就会立刻过来喂他们;如果他们想自己动手扣好外衣的纽扣,大人就会连忙过来给他们扣好;孩子要做什么都会有大人来代替他们做,非常残酷,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可是我们自己却在工作中对我们自己的权益非常敏感,如果有人企图取代我们,他就冒犯了我们。《圣经》中有一句话:“他的地方将被别人占据”,这句话是说自己的领地有丧失的危险。
如果我们成为一个不能理解我们自己情感的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巨人的奴隶,我们该怎么办呢?当我们正在安静地喝汤,在慢慢惬意地品味时(我们知道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会有这种乐趣),假如一个巨人突然出现,从我们手中抢走汤匙,强迫我们以最快速度把汤喝下去,以至于我们几乎被汤噎住,这时我们会提出抗议:“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慢点喝!”伴随而来的是从心底里感到受到了压迫,我们的消化也会因此受到损伤。再假如,我们正在一边想着一些愉快的事情,一边慢慢地扣着外衣的纽扣,此时你在自己的房子里享受着自由,从心底里感到无比幸福愉悦。突然,一个巨人凌空出现在我们面前,忙着帮我们穿衣服,而且巨人竟然一眨眼之间就把我们带出了家门。此时我们感受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外出散步能给我们带来的愉悦顿时消失殆尽。我们的营养来源不仅仅是我们吞下去的汤,也不仅仅是能带来身心健康的散步等体育锻炼,还来源于我们自由地做这些事情。我们感到反感,试图反抗,根本不是因为对巨人的憎恶,而只是因为我们的天性,出于我们在生活的所有方面对自由的认识。我们人类自身没有意识到,只有上帝知道,知道这种意识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人类的思想意识中,我们毫无察觉,而这种意识会贯穿始终。就是这种人类对自由的热爱滋养了我们的生活,甚至几乎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幸福安康。关于这一点曾经有人说过:“人不光是为食物活着,还为精神活着。”幼儿肯定是更加有这种精神方面的需求!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正在进行着创造!
为了捍卫他们生活环境的小小领地,他们不得不斗争,不得不反抗。因为每当他们想锻炼他们的感觉,例如触觉时,每个人都会指责他说:“别碰那个!”如果他们想从厨房拿点东西,例如拿些食品残渣做碟小菜,他们就会被毫无怜悯地赶到他们的玩具那里去。孩子的注意力集中之时,正是他们发展其精神活动的组织过程;孩子自发努力之时,也正是他们在盲目探索周围那些维持他们智力的物质之时,这是多么神奇的时刻啊,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却经常被粗暴地打断!难道我们自己忘记了那些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窒息着我们的事情,以及那些窒息给我们留下的痛苦记忆了吗?
虽然说不出确切的理由,但我们还是感到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我们被轻视并被骗走了一些宝贵的东西。也许正是在我们要创造我们自己的关键时刻,我们被大人们打断、被他们迫害,以至于造成了我们心理不健康、脆弱,甚至是不会生活。
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当中的某些成年人,他们不像我们大多数成年人那样成熟稳重,但是在精神的自我创造方面,他们却是天才。例如,一位作家突然有了写诗的灵感,这时他的仁慈、鼓舞人心的诗作就可以帮助别人;再以数学家为例,他刚要解出一个难题,而这个难题的解决会得出对全人类都有很大益处的新定律;我们再以艺术家为例,一旦他头脑里产生了他满意的理想画卷,就需要立刻画到画布上,以免一幅稀世的杰作丢失。想象一下,如果这些人在这样的心理时刻突然被某个粗暴的人打扰,朝他们高声喊叫让他们跟他走,还拉住他们的手把他们向外拉,或者用肩膀把他们向外推,去做什么?是去下棋,棋盘已经摆好了!哈,他们会说:恐怕再没什么事情比这更残酷的了!由于你的愚蠢行为,我们的灵感都没了,人类将因此失去一首伟大的诗篇、一幅传世名作、一个非常有用的发现。
在相同情况下,孩子虽然没有失去某个单一的事情或杰作,但是他失去了自我。因为他的杰作就是一个全新的人,他正在悄悄地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天才。儿童的“任性”、“顽皮”和“幼稚的自我吹嘘”也许就是由他那因被误解而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让人难以理解的不幸呐喊。
但是实际上他们不仅是精神受到了伤害,他们的身体也受到了摧残。因为一个人的精神会对整个身体产生影响,这是人类的一大特性。
在一个收养孤儿的慈善机构,有一个长得非常丑的小孩,然而照看他的那位年轻保育员却很喜欢他。有一天,这位保育员告诉一位女捐助人说这个孩子越长越漂亮了,这个女捐助者就跑过去看,但发现这孩子依旧很丑,她在心里想,也许每天相处可以使人习惯别人的缺点,所以那位保育员感觉他越来越好看了。过了一段时间,保育员对女捐助者又说了同样的话,所以女捐助者又很善良地来访了一次。保育员在说到孩子时的热情给了女捐助者很深的印象,她感触很深,认为是爱使得保育员看不到孩子的缺点。几个月过去了,最后,保育员带着胜利的喜悦心情宣布:这个孩子从此以后不可能有任何缺点了,因为毫无疑问他已经“美丽无比”了。女捐助人看后也大吃一惊,不得不承认这竟然是真的。在伟大的爱的影响下,这个孩子的身体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
我们经常用这种思想来欺骗自己:我们正在给予儿童一切,给他们新鲜的空气和食物。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这是因为锦衣玉食和新鲜的空气对一个人的身体来说是不够的;所有生理功能都要求更富足,所以生命的唯一关键就在于此。儿童的身体也要靠精神的满足愉悦而存在。
生理学告诉我们:在室外吃一餐便宜的饭比在空气污浊的室内吃一餐豪华盛宴要更有营养。因为在户外,身体的各个机能更加活跃,吸收也就更加完全。同样,与所爱的人和富有同情心的人一起进餐,远比与粗俗的不能忍受的部长一起参加一个喜怒无常的贵族举办的盛宴要有营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哭闹就说明了这些。在有些地方,虽然我们每天吃的是饕餮盛宴,每天住的是花园洋房,但我们的生命受到压制,在这样的地方我们不会健康。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