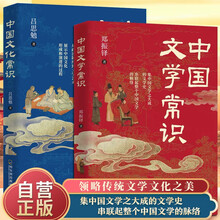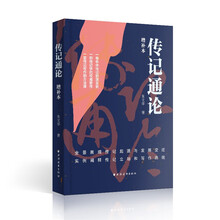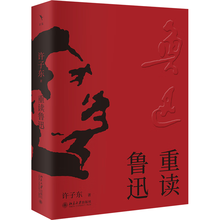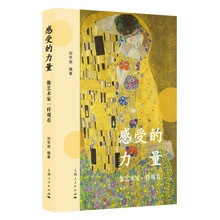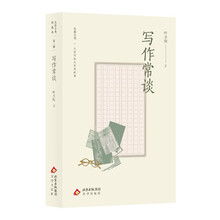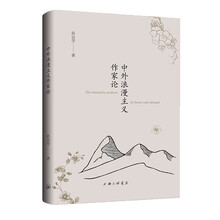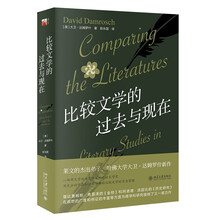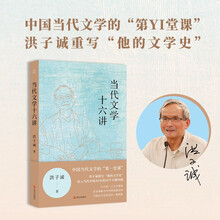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
不是每一种文化都能承受和接纳现代文明的震惊的。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悖论: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而又返回源头。
——保罗·里克尔
在贬低后现代主义的人中(如詹姆逊,《后现代主义者》;纽曼;伊格尔顿)存在一些共同特征;无论如何界定,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反历史的,这虽然令人吃惊却是普遍认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一致发起的熟悉的攻击,矛头不仅指向当代的艺术,而且针对当今从阐释学到解构主义的各种理论。最近,多米尼克·拉卡普拉(LaCapra,1985:104—105)站出来支持保罗·德曼的论点而反对弗兰克·伦特里基亚,声称德曼事实上强烈地感到了探究历史的可能条件的必要性,以及这些条件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如何得以实现。然而,引起我兴趣的,不是争论的细节而是事实的本身:历史现在又一次成为一个文化问题——而且这一次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看来,它无可避免地与造就了我们对当今艺术和理论的观念的整个受到挑战的文化与社会的种种假定连在一起:对源头与终结、统一与完整、逻辑与理性、意识与人性、进步与命运、表征与真理等的信仰,更不用说因果说、时间等质论、直线延续性和连贯持续性等诸多概念了(Miller,1974:460——461)。
这些质疑性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新颖,其思想根基早在几个世纪前已十分稳固,只是它们在当今的许多论述里受到格外关注而使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只有到了1970年,知名的历史学家才会如此论述:“小说家、剧作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诗人、预言家、学术权威和具有多种信念的哲学家,都强烈地表现出对历史观念的敌视。我们许多同代人特别难于接受过去时代和往昔事件的真实性,顽强地抵制种种对历史知识的可能性或实用性的论断。”(Fisher,1970:307)几年之后,海登·怀特宣称:“当代文学的鲜明特征之一在于执著地坚信:历史意识必须抛在脑后,如果作家想严肃地审视人类经验中那些现代艺术特别要揭示的层面。”(White,1978:30)而他引述的例子很说明问题,他引的都是大名鼎鼎的现代主义人物——乔伊斯、庞德、艾略特、曼等——而非后现代主义者。然而今天,我们自然必须对这类的声称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因为有了迈克尔·格雷夫斯和保罗·波尔托盖西的后现代主义的建筑,有了像《马丁·盖尔的归来》和《雷德尔中尉》这样的电影,有了我们称做“史述元小说”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的作品,如《G》、《羞耻》和《异想天开》。当今似乎有一种进行历史性思考的新愿望,但是历史性的思考便意味着批判性的和语境性的思考。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