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投资精英的晚餐会—闯进刺猬丛
三角是一家投资俱乐部,会员差不多每月聚会一次,共进晚餐。虽然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亲切愉快,但实际上他们是全美国明争暗斗最激烈的一群人。
昨晚,我到“世纪”去参加了三角投资俱乐部的晚餐会,与会者大约25人,一半来自对冲基金,另一半则是些非常激进的单向多头基金经理。年龄组合也平分秋色,既有满头银发、语气沉稳的耆宿,也不乏新潮时尚、说话飞快的青年。无论老少,这里每个人都是投资界的风云人物,正管理着这样或那样具有竞争性的公众财富。
三角是一家投资俱乐部,会员差不多每月聚会一次,共进晚餐。吃饭时大家交换一下心得,互相探探底细。我不常去。去那儿得有合适的心情,得一直挂着作秀的表情。因为虽然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亲切愉快,但实际上他们是全美国明争暗斗最激烈的一群人。大家的交流和谈话显然都带着戒心。反正,这绝不是那种可以放松一下的老友会。
昨晚和平常一样,大家先站着边喝边聊了大约半小时,话题集中在现在赚钱有多难上。我和乔纳森聊了聊,他如今是炙手可热的对冲基金精英,整天坐着自己的湾流喷气机飞来飞去,身价估计高达10亿。当年,他还在朱利安·罗伯逊传奇般的老虎基金里当一名年轻分析师时,我就认识了他。我喜欢他,他是那种脑子里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
昨晚他不停摇头。还有一星期就是他大女儿的10岁生日,他问女儿,为这个年龄跨入双位数的大日子想要点什么礼物。她盯着他问:“要什么都行吗?”“对。”他说。“那你可别害怕,我的愿望和飞机有关。”他呆住了。自己都做了什么?可怜的有钱小姑娘!她已经想要一架自己的飞机了。“好吧,是什么愿望呢?”他磕磕巴巴地问。“爸爸,”她说道,“我都快10岁了,可还从没坐过一次民航飞机。除了我,学校里所有的女孩子都坐过。我最想要的就是让你带我去一次真正的机场,换登机牌、过安检、排队、让人搜身,然后坐普通飞机去一个什么地方。爸爸,连一次民航都没坐过真是丢人。”看来,有孩子的“刺猬”真是不容易。
多嘴、贴金和砍人
然后,我们走向一张布置着蜡烛和鲜花的长桌,准备吃晚饭。昨晚晚餐会的主席是利昂,他简单说了几句之后,大家开始轮流发言。通常的规矩是,每人用不到4分钟的时间谈一谈最近看好的股票或概念,并说明原因。每个人发言时,别人都做笔记,但很多人是在胡说。还有不少家伙一吹起来就滔滔不绝,这时主席就得无情地斩断他的发言,否则大家整晚都别想走了。有些人认为这些晚餐会让人颇受启发,可我从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度过一个这样的夜晚之后,你确实能了解到会员们的情绪怎么样,以及哪些领域正在成为热点。
昨晚我却被弄糊涂了。多头和空头两派意见势均力敌。有的故事想象力丰富,充满了大胆的推测。说到能源热时,一个小伙子讲的故事让人难以置信,说是马来西亚一家石油钻井公司正在婆罗洲近海搭起钻探平台采油,而这个海域已经可以与北海媲美。他就是这么说的!一个共同基金经理则谈到了一种新的外科手术方法,据说可以使前列腺手术后丧失性功能的风险降低75%。然后,大家照例说起了不同时期的互联网奇迹,以及从健康食品连锁店到纳米技术的各式奇谈。
因为每个人都要推荐自己实际持仓的股票,所以多数人都在一开头说明自己的仓位。轮流发言时,下面当然少不了冷嘲热讽—不是嘟囔着说那几个出名爱捣鬼的家伙又在“贴金”,就是开玩笑地嚷嚷一句“砍人啦”!“贴金”就像它听起来那样—你把一个故事带到聚会上,把它说得天花乱坠,故意夸大一些基本面,当然那是对你有利的。换句话说,比如你想推荐赛门铁克的股票,说它明年的赢利会很高,现在股价便宜,到了晚会上,你可能会把赢利预测从每股3.50美元说成3.75美元,而实际上,每股3.30美元就已经算个小奇迹了。不过,谁能说准一家远在天边的科技企业赢利是多少,干吗不做做美梦呢?
贴金相对来说不算什么大罪过,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经常这么做。不过,会员们的鼻子非常灵,谁要是贴金贴得太过分,他的信誉就算完了。而且,如果还有别人了解你正在讲的故事的底细,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你打断,纠正你的夸大不实之处。这可相当尴尬,但这也正是这类聚会的魅力所在。如果某人讲了一段新鲜有趣的故事而又没被打断,那就说明这个故事至少很新,而且,有可能是真的。
“砍人”是严重得多的罪行。如果你当场被拆穿,也就是所谓的“人赃俱在”,你甚至可能被踢出俱乐部。砍人是指你在讲故事时故意给它贴金,希望吸引别人去购买,而你却在暗中吐出那种股票。介绍自己做多或做空的股票是一回事(而且多数会员都会说明他们拥有某种仓位),砍人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砍人是说谎,是诈骗,是对这场金钱游戏规则的冒犯。
像蛇一样令人讨厌并不说明他不会赚钱
曾经是俱乐部会员的理查德素有砍人的嫌疑。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但又很难被证实。只要没人受害,大家也就不太在意了。顺便说一句,理查德属于那类坚持不让别人管自己叫迪克①的人。
在名声赫赫的对冲基金业中,有一群狡猾的家伙靠出卖信息甚至各种内幕消息赚钱。理查德的狡猾绝不逊色于这些人,别看他有着一副体面有教养的哈佛毕业生外表,穿着雅致的套装,说话时带出一丝波士顿腔。但是,像蛇一样令人讨厌并不能说明他不会赚钱。理查德混迹于俱乐部很久,另外一名会员甚至还和他做过一阵子买卖,最后以一场纠缠不清的官司告终。理查德有一次得意扬扬地说他是“自己造就了自己”,他的前合伙人在一旁插话道:“而且你崇拜你的造就者。”理查德非常精明,也非常招人讨厌,他挣了非常多的钱,这些钱他多数留给了自己。他在谈论股票消息时,总是说得十分确凿和细致,我猜这就是我们容忍了他那么久的原因。
多年前,理查德和我打过四五次网球单打,那是恐怖痛苦的经历,虽然我明知道自己比他强。如果我击出的一个球落在界内但靠近底线,他经常会(当然不是永远)高喊“出界”。要是他击出的一个球明摆着出界了,但超出底线的距离不超过几英寸,他会跑到网边,费力地向落点张望。这样会弄得你不好意思,甚至不敢宣布球出界了。在我连续得分时,理查德会坚持走到场边坐一会儿,系上5分钟的鞋带。有时,他就此把比分记错了,当然错得永远对他有利。
我和别人说起这些,他们也曾有过同样的苦恼。有人告诉我理查德还有一次在对手领先三局时要求重新开一盘—老天!对付理查德的困难在于,难道你要认真跟他理论、说他捣鬼,好让别人看热闹?不,那太丢脸了,旁边球场上的人听到了会觉得你俩都是白痴。所以,你能做的只有小心翼翼地击球,不让它落到靠近底线和边线的地方。每次和他打球,我都下决心这是最后一次,但他会逼着我再打一场。就像我说的,本来明明知道一定能赢他,但他做的那些手脚太过分了,弄得我心烦意乱。最后,终于在打第四场时,他赢了。比这更让人恼火的是,他立刻就去四处宣扬,好像他总是赢我一样。
终于有一回,理查德在三角俱乐部玩儿得过火了。那是几年前的一个晚上,他透露了一条诱人的消息,说是一家公司刚刚研发出一种没有副作用而效果显著的减肥药,尚秘而不宣。只要每天吃两次、每次一片,很快,一个月后你就能减掉10磅!这显然将成为轰向肥胖美国人的一枚重磅炸弹!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到了盲测结果,还引用了斯坦福研究集团和美国药品协会的数据。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的批文马上就能拿到。好几个人都知道那家公司,那是一家正规的生物科技企业,也颇有几名像样的科学家,只是财务状况不怎么乐观。那家公司曾经宣布自己正在研制一种有前景的减肥药,但生物技术分析结果不明。
不少人被这条消息迷住了。如果他们一起行动,生物科技股肯定坐上火箭。理查德被细细盘问,但他应付得不错—我跟你说过他是多么机灵。“瞧,”他说,“辉瑞制药公司原来的董事长现在是斯坦福的一个头儿,我都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们都知道关于基因这种事没法说得太准,不过他告诉我大量实验证明这种药片对老鼠很有效,最棒的是它没什么副作用。老鼠比平时撒尿撒得多了,但体质没什么变化。你们随便吧。我反正是重仓,还得再吃进。”
第二天,有几个人下了买单,但让他们有点意外的是立刻就成交了,而且量很大。两周之后的一天早上,当这家公司突然宣布已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撤回药品申请时,他们的感受就不仅仅是意外了。这些药的确让老鼠减了重,但也让它们得上了无可救药的胃癌,都死了。股价立刻崩掉。接下来的一次聚会时我在,理查德没来。吃饭时,一个叫约翰的,也就是那群买了股票的家伙中的一个,谈起他的单子一下子成交时他曾多么疑心。后来他查了那个大卖主是谁,结果发现就是理查德常用的那名经纪!
会员们坐在那儿面面相觑,那情形就像一群牛仔终于弄清了谁是偷牛贼。约翰是个严肃的大块头,第二个月晚餐会前的鸡尾酒时间,他和另外几个人遇到了理查德。理查德吞吞吐吐地说他只卖出了一点股票来减轻仓位。“滚出去,你这垃圾!”约翰低声说。理查德走了,他再也没来参加过聚会,我听说他搬到了洛杉矶。
外面有一个丛林,而刺猬们正在杀死它们的金鹅
昨晚饭后,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聊起了对冲基金。我们这些三角俱乐部的会员、投资战场上的老兵,谁都不羞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况且,我们已相熟多年。一时间难听话满天飞,密度赶上了巴格达不走运的日子里空中的榴弹。一开始有人说起现在美国有8000只对冲基金,资金规模在1990年还是360亿,如今已差不多有1万亿。一个单向多头基金经理酸溜溜地抱怨了一大串:“对冲基金的黄金年代快要终结了,而且会天崩地裂地结束,绝不会无疾而终。资金的规模越来越大,基金雇用的人才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从资产类别到个股,一切一切的定价都被疯狂的投资者严密监视着。这些人整天盯着电脑屏幕,拥有大量数据库,用光速转移大把金钱。结果就是价格被哄抬,投资收益减少。很显然,从前那种绝佳的套利机会现在差不多还没出现就蒸发了。事实上,大家可以抓住的机会就那么多,现在被分散到更多只基金、更大量的资本上,所以对冲基金作为一个资产类别来说收益降低了。同时对冲基金的风险又在加大,因为大家的仓位都更大更集中。你们这些贪心的刺猬正在杀死你们的金鹅。现在的情况不是有点危险,而是离死期不远了。”
“你不就希望这金鹅比你想象中更不值钱,病得更重吗?”一位喝着白兰地酒的对冲基金经理说道。
“宏观基金就是导致破产的罪魁祸首。”另一个人说道,“新进入的资金太多了,你的动作一定要快才行。”他盯着我。
“现在宏观基金已经强手如林,”他接着说,“太多的人在玩儿这个,加上那些胆大的投资者,简直是在互相残杀。过去6个月就冒出来大约100只新的宏观基金,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下一个斯坦·德鲁肯米勒或刘易斯·培根。这些人里有的实在太嫩了,他们的愚蠢会误导你。偏偏这些家伙又财大气粗,要想跟他们硬碰,倒霉的是你。除了这些人,还有那么多大投行的资产交易部,加上各式劣迹斑斑的央行,像什么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啦,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啦。上星期我就被一家亚洲的中央银行和几个新的宏观基金经理给整惨了。全都是些笨蛋!”那个宣称自己被整惨了的家伙看起来意气风发,我没吱声。
“这就是金钱赌博!本来大家玩儿得好好的,谁知道新加进来的人越来越有钱,出手越来越快,结果是这游戏越来越难玩儿、越来越危险了。”另一个对冲基金经理闷闷不乐地说,“每个人都像吃了激素,拼得一天比一天惨,简直就像橄榄球联赛。”
“越来越多的基金根本挣不到超额回报,还收那么高的管理费就缺乏说服力。”另一个家伙说,“太多的资金涌进来,基金的表现记录要被毁了,投资明星的光环也要被毁了。这之后,大家对对冲基金的热情也就注定要冷了。整个对冲基金业的利润池还是那么大,喝水的人可是越来越多。甭问,下一个进棺材的就是你。”
“你说利润池没扩大,对这点我倒不是很肯定。”我争道,“就说这些懵懵懂懂刚闯进来的新手吧,胃口不小,经验不足,大多数得交点学费。他们亏的钱就是咱们这些人利润池的进项。”这时我发现一名基金老手正瞅着我,面带一丝诡笑。估计他脑子里在想:“你算个什么,小子,还在说别人嫩?”
“杠杆、杠杆、杠杆—你们这些人可能就要毁在这上面了。”那个单向多头基金经理说,“其实,自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带着它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和花里胡哨的尾期选择权(管它是什么东西)垮台之后,对冲基金已经在削减杠杆了。反而是投资者—既包括个人也包括组合基金—在加大杠杆。客户对于越来越低的回报不满意,于是组合基金就跑到银行去借钱。而银行(尤其是那些欧洲银行)非常乐意借贷给这些富有的个人客户,让他们去加大手中对冲基金的杠杆。从理论上说这没错。一揽子多样化的对冲基金比一只基金的波动性要小,所以,干吗不用杠杆来扩大回报呢?”
“是啊,”另一个声音说,“但是等到哪天晴空霹雳、山崩海啸的时候,你就知道厉害了。对冲基金组合缩水10%所用的时间不是一年而是一个月,而一只大量运用杠杆的组合基金经过一次震荡就能损失15%。那时,整个对冲基金世界又会怎样呢?我来告诉你们吧:吓破了胆的组合基金客户会忙不迭地赎回,这样组合基金也得跟着从对冲基金那儿赎回,于是整个资产类别大缩水。而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采用多空策略的市场中立基金也都得跟着完蛋,因为在大家都被迫兑现的时候,他们的多头会跌价而空头却会上涨。”
“反正全得玩儿完。”那个单向多头基金经理说,“我这不光是说给你们,是说给大家,包括我。”一个晚上就这样结束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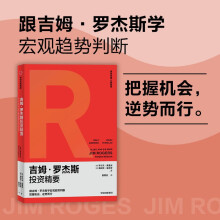






——大卫·F·斯文森,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
自从科技股泡沫的辉煌时代以来,投资已经成为一项有风险的工作,经营对冲基金更是如此。在本书中,比格斯透视了这些每天决定巨额资金投向的对冲基金人士的性格和心理。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它充满了趣闻逸事,也呈现了一个绝对内部人士的深刻见解。
——安迪森·维金,著名金融专栏作家、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