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沉甸甸的学术传记,让这位长于伪装的天才人物以本真面目示人。一次激荡心灵的阅读体验。
我由项峰开始,然后一直走着下坡路。
——奥逊·威尔斯
无论出于何种原由,威尔斯留给我们的只是关于他自己的一些碎片。而我,试图把它们拼接起来。
——作者
唯有(《人生故事:奥逊·威尔斯》)这种别有意蕴的表达方式,才能更为完整、准确地传达作者对奥逊·威尔斯其人其作的理解,所得结论比起依据旁人评论或者威尔斯的自说自话来得更为坚实,且直指灵魂深处。
——译者
1. 奥逊·威尔斯是电影专业人士心目中最伟大的天才,他这个名字就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2. 《人生故事:奥逊·威尔斯》的切入点甚为特别,在讲述威尔斯人生故事的基础上,着手对他的这些故事进行调查研究。
3. 国内读者将首次看到的首部对威尔斯的评传。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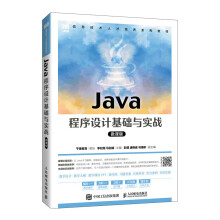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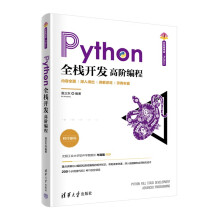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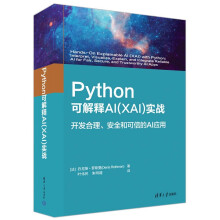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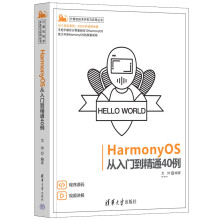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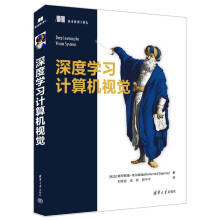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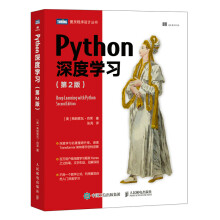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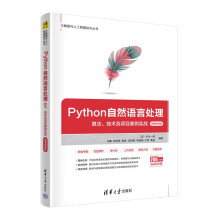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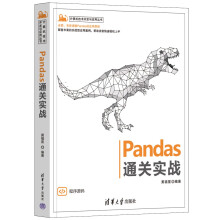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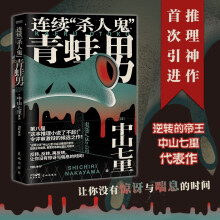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威尔斯 留给我们的只是关于他自己的一些碎片。而我,试图把它们拼接起来。-作者
唯有(本书)这种别有意蕴的表达方式,才能更为完整,准确地传达作者对奥逊·威尔斯其人其作的理解,所得结论比起信据帝人评论或才威尔斯的自说自话来得更为坚实,且直指灵魂深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