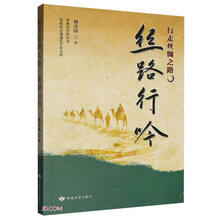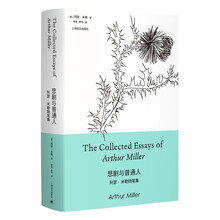二、学术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从1964年的“四清”到“文革”的六七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我的学术研究完全抛荒了。1974年,学校(湖南师范学院)组建政 史系,校领导任命我为该系党总支副书记①。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但我在经历“文革”的反复折腾后,对政治已心灰意冷,而且对“文革” 本身也渐有反思。当时,校领导对我仍很信任,拟升迁我为教务处副处 长,或表示要将我所任副职升为正职(即由总支副书记升为书记),我都 以“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为由婉言谢却了。此时,我是“身在曹营心 在汉”,即表面在抓学生的政治思想管理等工作,但内心深处却向往学科 专业工作。虽然在那个年代,钻业务也同样有风险,膏火自煎者多有,但我认为它至少可消解一些疲惫,让精神有所依托。在这种心猿意马的 精神状态下,学校开干部会我常溜号,我分管的学生工作也搞得很糟,纪律废弛,学生旷课、斗殴等违纪事经常发生。消息不断传到校方,校 领导发现我终究不是政治上的有用之才,打消了提拔我的念头。由此,我也获得了自主择业的机会。1978年政史分家后,我留在历史系,主动辞去了副书记的职务,选 定中国古代史作为我从事的专业,并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的部分教学。我之所以选择中国古代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不是偶然的,因为1974年以 后,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解脱,我曾潜心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或者说 补过一段课。恰当此时,我得到了紧邻中文系已退休的李之透老师的大 力帮助。李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的名宿。他的“以校为家,校胜于家,以 生为子,生胜于子”的教育理念,艰苦办“广益中学”的奋斗精神,长 期为学界称颂。在与他接触中,我又发现他是位宅心和厚、学问笃实、学养有素的学者,只是由于荒唐的政治原因,长期被冷落,成了一介 “逸民”。由于我拜师志诚、心切,李先生答应尽量满足我的要求。他以 教育家的仁爱、学问家的睿智,雅意勤勤为我补习了几年“国学”。我对 《说文解字》的细读,对先秦经史子集的钻研,都是在他的精心指导下进 行的。日就月将,我具备了较为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因此,1978年开始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的教学时,并不感到突然。我在执教“历史文献”时,因工作的需要,阅读了好些先秦古史论 著,特别是郭沫若的史学论著读得最多。由此,认识到:郭沫若不仅是 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是 位学识渊博的文化大师。我想重操旧业,继续对他的著作进行研究。甚 至想,纵令研究不能有成,追随大师的足迹走一遍也是值得的。怎样进 行研究呢?在中外著名学者治学之方的启示下,此时,我头脑中渐渐形 成了这样几点看法:首先是研究郭沫若这样具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的文化 大师,要广泛占有与研究客体相关的一切资料,不仅是直接材料,而且 包括间接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对郭沫若有完整的认识。为此,我设立 了一个小小的郭沫若研究资料库,以“涉猎式”的泛读法将日积月累的 资料置入库中,并对资料作出初步的区分与会综,即把不同材料作分门 别类的处理。其次,不仅要通读郭沫若所有的著作,而且要读他本人读 过的书,特别是要精读对他影响甚大的书①。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他的思 想学术和创作脉络,才能有所发现。为此,我沿着郭沫若自述的线索,开出了一个长长的郭沫若的读书要目,然后一本一本找来读。我把这叫 做“辐射式”的读书法。而在阅读每本书时,又采取由逐字逐句细读到 钩玄纂要直至出以己见的“掘进式”的读书方法。如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对于大小徐本和段注《说文解字》,我曾反复钻研,以求得一把籀读郭沫 若甲金文考古论著的钥匙。在史学方面,郭沫若盛为称赞的《观堂集 林》,我看过多遍,发现郭氏对王氏的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文学 方面,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我也曾一读再读,因为郭沫若在与徐迟通信中曾详细说明这几个剧本与史剧《屈原》的异 同。由此,更引发我对古今悲剧做初步的探讨。为了研究郭沫若的早期 哲学思想,我将被郭沫若称为“泛神论者”的庄子和斯宾诺莎的著作反 复比较,发现两人的思想体系实不相同,郭氏把他们都称为“泛神论 者”,实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②。在政治思想方面,我将郭沫若早期 最为称道的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看过三遍,因为郭 沫若说过:他翻译此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转折点。再次,我认为 研究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名人,不能局限于个别方面,而要把他作为一个 整体来研究。我这种“整体研究”的想法,实受中国哲学独特的思维方 式——辩证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把对象看做一个整体,认为 整体的各部分都有此动彼应的密切联系,而一切对立都有其统一的关 系),但更多是仔细研究郭沫若作品后所解悟到的。例如郭沫若是文史兼 通、文史相融的大家,他的历史研究往往是为史剧创作作准备;反过来,他的史剧创作又常常丰富了他的历史研究的内容。如果研究者不是文史 兼修,对他作品的价值就很难作出科学的阐释。这种“目有全牛”的看 法与古代哲人所称颂的“目无全牛”的境界,并不矛盾。因为“目无全 牛”是庖丁经过三年分解牛所达到的技艺纯熟的境地,而“目有全牛” 则是他解牛时首先应注意到的,否则,那真是“盲人摸象”了。从1974年下半年起至1978年郭沫若逝世前的几年,我就是秉着上述 学术观念寒暑无间地进行学习研究的。这段时间,我在政治上临深履薄,严守分际,但在求知上格外努力,这是我有生以来笃学不倦、进步最大 的几年。其攻读之刻苦,较古人的“韦编三绝”、“悬梁刺股”、“三年 不 窥园”、“焚膏继晷”,实未遑多让。其嗜学入迷之情景,亦如韩文公所 言:“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答李诩书》)至 今,我还记得当年废寝忘食学习的情景:夜阑人静时,在李先生不到五 平方米的斗室里,我还在听先生孜孜不倦地讲解《说文》,直至师母梦醒 后提醒我们“该睡觉了”,才“下课”。在天麻麻亮的清晨,肉店门前已 排成一条争相购肉的长龙,夹在长龙中的我,仍手拿《说文》,一个个记 诵书中对每字的说解,有时连买肉的事也忘了。在玄冬修夜,我看书常 过夜半,屋里没有取暖设备,冷得哆嗦时,就靠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或把手放在嘴边哈口气和以电灯泡焐焐手。有一次,我在床边洗脚,边 看书,因实在太疲倦了,竞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但脚还在水盆里。妻 子发觉后,才把我叫醒。三、穷山沟里的经世致用之学 在几年刻苦攻读中,一件偶然的事,中断了我的书斋生活,特别是 中断了我的“郭研”。那是1976年下半年至1977年,我被派到湖南省委 “农业学大寨”沅陵分团工作。熟悉这一段历史的都会知道,那是一个特 殊的历史时期:毛主席逝世不久,“四人帮”已被打倒,但“左”的指导 思想还未得到纠正。即如这次“学大寨”运动,其口号就是“以阶级斗 争为纲”、“大批促大干”、“三年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P6-8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