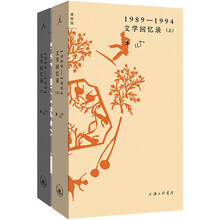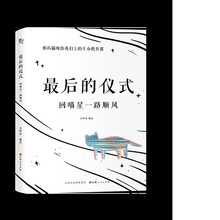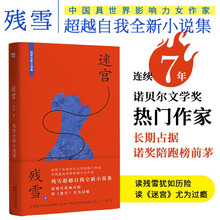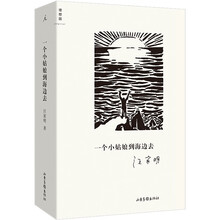寥落丁香入梦残
我特别喜欢有雨有雪的天气,当然,是指北京的雨雪。这 雨丝、雪片和着钟鼓楼的晨钟暮鼓,与童年的回忆萦绕裹缠在一 起,常常人梦。这样的梦,一梦就是几十年。儿时搬过几次家,但都在钟鼓楼附近打转转。最早是旧鼓楼 大街,而后是纱络胡同,好像还嫌不够贴近,最后冥冥中一只大 手把我们一撮,撮到鼓楼脚下的叫天胡同。前后几次搬迁,实际 上是由一个四合院搬进另一个四合院,始终没离开钟鼓楼。冰心先生说:“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 时含泪的微笑。”此刻,苍古缥缈的晨钟暮鼓又仿佛响起,多么 遥远的记忆啊——钟鼓楼,四合院,雨雪天,儿时的梦,当然,还有梦中的丁香。一如老照片,时间越久远,老旧黄暗得越厉害,模模糊糊 的,最终化成岁月的屑片。对旧鼓楼大街和纱络胡同的记忆已经 不很真切了,如今印象最清晰的是叫天胡同。确切地说,这是座“三合院”,没有南房。街门对着西跨 院的月洞门,南墙脚下种着一溜丁香。从街门右拐进了二门,迎 面是一个粉墙影壁,青砖墁地的院子,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 问。南墙根儿又是一溜丁香。北京的冬天干冷干冷的,一阵北风 卷来,里院外院的丁香纤细的枝条瑟瑟发出一片碎响。房子刚刚 买过来,爸指点着说,外院种的是紫丁香,里院都是白丁香。我 无从想象这房子原来主人的样子,可他多懂得丁香啊!为了这满 院的丁香,为了那位懂得丁香的人,我更喜欢叫天胡同的这个新 家了。六十几年前也是讲“装修”的。除了屋子的顶棚和四壁雪洞 似的裱糊一新外,门窗廊柱也都从新漆过。竣工时,爸携我坐三 轮儿来“验收”。爸从小疼我,见我对檐下枋粱上油漆彩绘的花 鸟虫鱼大感兴趣,特嘱师傅给我画了幅松鹤图。我还记得画儿画 在一张高丽纸上,丹顶鹤活了似的,不错眼珠地盯着我……我小 心地捧着那张纸,脚都不敢抬,就小步蹭到“画家师傅”跟前,给他鞠了个大躬。记得过后爸说,他算不上画家,不过一个画匠 罢了。可在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眼里,画家与画匠的概念其实是一 片混沌的,他小小的心只认这只鹤,真拿幅李苦禅的鹰来,说不 定他还会摇摇头舍不得换呢!记得是腊月里搬进叫天胡同的,安排停当后,一场瑞雪适时 而至。一早掀窗帘看到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我大叫一声“下雪 啦”,兄弟姐妹们炸了窝,像雀儿似的一蹦而起,你争我抢地冲 到院里去看雪,然后慌忙地洗把脸,吃口东西,就又爬回到大床 上。像这样的大雪天,别人家的孩子早就玩儿疯了,打雪仗,堆 雪人,滚雪球……我们家却不,我们有独一无二的玩儿法。逢着 雪天,平时野马似的我们,却都会乖乖地围坐在爸身边,守着火 炉子,喝妈泡的焦枣儿茶,嗑妈炒的喷香的红西瓜子儿,听爸讲 故事。爸的故事滋润着我们长大,而今又频频入梦,把梦也滋润 得分外香甜,像妈头天熬一夜熬出来的腊八粥。爸一米八二的个头,高颧大眼,鼻直口方。他出身寒微,原 来的名为治农。爸的治身格言是:“文一份武一份,文武皆能治 国;耕半日读半日,耕读均可齐家。”但时逢乱世,军阀混战,爸遂弃耕从戎,自己改了名,叫“更武”。上天仿佛有意作弄,无论“治农”还是“更武”,可叹爸都没什么成就,但子嗣倒颇 为兴旺。前一个妻子撒手西去,留下三个儿子。我妈是继室,又 生了我们七个,四男三女。虽是造化弄人,爸却能安常处顺,他晚年喜欢苏轼“治身 不求富,读书不为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的诗句,恪 守“子不教,父之过”之道,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对子女的教 育上。爸给我们立了很多规矩,比如,“食不言,寝不语”,“饭 要八分饱,壶要七成满”,又比如,“用过的东西,从哪儿拿的 放哪儿去”等。爸自奉甚俭,一生茹素,不沾烟酒,常把“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万物维艰”挂在嘴边。爱 惜粮食,不准掉饭粒儿,自然也是规矩之一。其他的规矩还有 “兄宽弟忍,姐友妹恭”,“低声唤,高声应”等。我们十个的 小名都有个“得”字,男从土,女从心,像得塬、得地、得意、得慧……爸说,小名因为好记、好唤,故专为父母所用,我们彼 此是叫不得的,否则就是不友不恭,·就是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就 要接受教训。爸有两件东西是不离左右的。一个是布掸子,泥猴似的我们 进屋之前,爸必得用布掸子挨着个儿把我们从头到脚抽打干净。另 一个是戒尺。用戒尺教训顽童并不新鲜,鲜见的是爸独创的“自己 打自己”的方法。具体打法是,伸出自己的左手(必须是左手,右 手还要留着写字),右手执戒尺,打一下,还要问自己一句:“下 次还敢不敢再……”为着以儆效尤,一个挨打,别个都要排成队肃 立两旁。三妹、九弟一贯顽皮,自责的声儿高,戒尺举得也高,最 终却在手心轻轻一比画了事,反招得旁观的我们捂着嘴窃笑。爸这 时就要夺过戒尺来亲自“执刑”,尺一击,娇嫩多肉的小小掌心旋 即红肿起来,令站在一边的我们无不悚然。这时爸就会丢开戒尺,用早已备在一旁的碘酒棉球在孩子们肿起来的手心上涂抹,以示关 爱。但每每至此,早憋得红头涨脸的“受刑者”,都会发出长长一 声号叫,痛哭起来。不完全是因为手心的疼痛,而是因为心里头很 深很深的那种无地自容和愧疚。人为万物之灵,再幼小的孩子,也 是有羞耻心的呀!爸活到九十岁,仍腰板挺直,眼不花,齿不摇,最后无疾而 终。简单直白的爸怎会想出“自己打自己”的招数来管教自己的 儿女呢?思来想去,唯有一句古语可以诠释,叫做“爱之深,责 之切”。爸是爱我们的,就跟鸟儿对它的幼雏一样,有根草棍儿爸也 要“叼”回家来。爱我们的爸其实也是很可爱的,尤其是讲故事 的时候。他在床上盘膝而坐,双目微合,拖着长长的声调,上身 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而轻轻晃动……六十年过去了,爸去世也已 十七年了,但爸双目微合的神态历历在目,拖着长音儿的声调仿 佛仍响在我耳旁。P7-10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