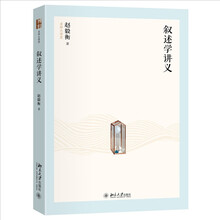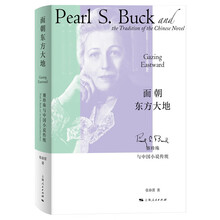“我”以自身的温热唤醒了“死火”,“我”又指向了谁?因为现实太寒冷,因为(诗人自我的)内心世界太寒冷,环顾四周,诗人找不到支撑自己站立起来的力量或因素,坠入冰冷绝望的深渊中,几近死灭……就这样被自我内心的阴冷感觉压下去,沉入深渊的谷底吗?不甘心,这样是不行的——诗人回答自己,于是,在外界寻觅不到,那么就从自我内心中汲取热力,以自身之温热唤醒自己(觉醒了的自我),这是典型的鲁迅式做派,即鲁迅所赞赏的“无赖精神”(无来由地,或就是如此),所以,其中的“我”也是作为先觉者鲁迅的一个侧影(另一个自我),更是唤醒先觉者(或战士)的先觉者。——从自身中汲取热力,以此抗拒阴冷,反抗黑暗,反抗绝望,反抗死亡,这是《野草》文本的一个基本结构方式,从其第一篇《秋夜》就开始了,突兀地出现的“枣树”的无来由的挑战,向凛冽的夜空的挑战,就是如此,就是诗人从自身中汲取力量的产物;至《好的故事》中,渴求温暖的诗人甚至幻化出一整篇被温润包裹着的美的人和美的事,并以此抗拒“昏沉的夜”和灰冷的心境;至于“我”碾死于“大石车”下,“我”是一个肩住黑暗闸门、富于自我牺牲的先觉者的隐喻,他更清楚自己的悲剧性使命——与整个旧世界(大石车)同归于尽,是从鲁迅心灵深处幻化出的又一个自我,这个“我”与《影的告别》中选择沉没于黑暗中的“影”,其意识特征是同构的。总之,“死火”和“我”是鲁迅内心中两个自我的象征,是一个鲁迅所分裂成的两个不同角色(身份)而已,鲁迅借助于这一有力的结构方式,力图呈现出一个心灵深处充满着矛盾冲突、正在进行着激烈搏斗的灵魂的全貌。这是《野草》的基本结构,已触及《野草》意象的歧义性、层次性和整体性问题。不甘心于死灭,而觉醒;觉醒之后,又面临着死亡;不甘心于这一死亡,而挑战死亡;凡此,都显现着鲁迅个体生命意志的勃发!
《死火》并非“爱情诗”,还有一个更有力的佐证:1919年鲁迅写下了一组《自言自语》,也是散文诗,内有一首不可同日而语、但可视为《死火》雏形的《火的冰》,作为“死火”这一关键意象的雏形此时已经形成:“遇着说不出的冷,火便结了冰了”;“火的冰的人”。这时候,许广平远没有出现在鲁迅的生活中;所以,它确切的寓意应该是关于先觉者及其人生境遇的。“爱情诗”变成了无稽之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