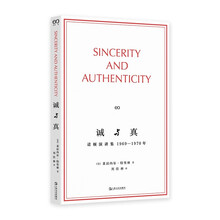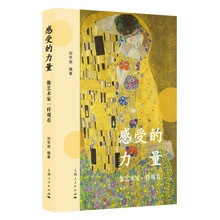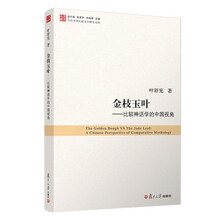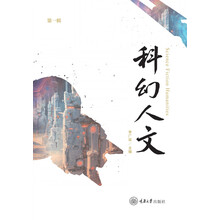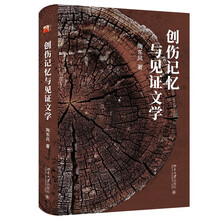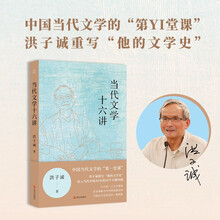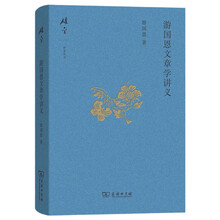寄托中的情感是一个动态系统,因此某些作品里,尽管只是在局部借个别意象或事件来寓意,但这意象或事件所载情感始终处于一种流动过程中,所以这“个别情感”即是整篇作品的“整体情感”。这便是寄托只能为体而不能为用的原因。象征(不自觉)中的情感已经升华为某种静态观念并凝结在相对应的物象里,这物象就成了比较稳定的、有特定意义指向的意象来使用,具有某个词或句子相似的独立表意功能。这便是象征可以为用(局部象征)的原因。
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学里,寄托、象征经常并用。这样既能防止情感一味地袒露,又可克服形象过分隐蔽晦涩,使作品隐显适度、虚实相生,产生出一种“全新的平衡”。如辛弃疾《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全篇所寄托情感比较显露,但局部却以“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象征南宋日趋衰微的国势,以“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象征政局的险恶和危急,使作品产生半透明的美感。骆宾王、李商隐的咏蝉之作,都是寄托为体、象征为用的典范之作。
寄托中的局部象征有两类,一类是积淀了具体的社会内容并已被读者反复体验过,因而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用于任何作品中都不会改变其特定的内涵。如“西北高楼”和“斜阳断烟”意象,对于南宋人来说,分别是故国和衰微国势的象征。又如菊花对我国读者来说,是一种高洁品格的象征:樱花对日本读者来说,是国魂的象征,等等。另一类是只是浸染强烈的主观感情,或者暗寓个人的身世,或者是特定环境中主观心态的外化。只有联系作者身世和具体作品,才能大致把握其特定的内涵。如宝钗和黛玉的《咏白海棠》诗,都暗寓了各自的身世和志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