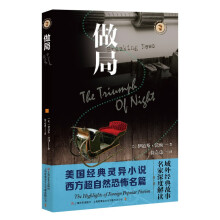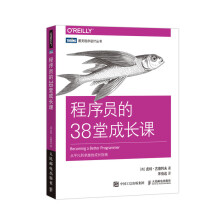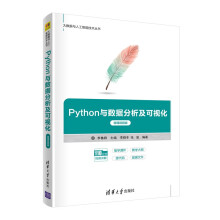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两汉之际社会与文学》:
班固传赞强调个人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这在《汉书》中屡见不鲜,前人论述颇详。这种强调可能有受《老子》影响的因素,更多的恐怕还是命定观在起作用。《汉书·司马迁传》赞日:“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跻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汉书补注》引何焯日:“此赞本叔皮之论。”苏舆日:“自呜呼以下,则固自撰,详玩后书固传论词可见。”无论班彪班固,对明哲保身的强调都是由命定观自然推导而来,盖命定观强调对先天已定的个人性命的敬畏,明哲保身自然是个人行为的第一要义。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因着命定观,对先天确定的性命有种敬畏而甘心服从。这种敬畏与服从甚至使得班固有不少违背儒家教义的言论。《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赞日:“何武之举,王嘉之争,师丹之议,考其祸福,乃效于后。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贤之爱,疑于亲戚,武、嘉区区,以一蒉障江河,用没其身。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此赞言论出班氏性命之论而大违儒家教义。班氏以为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之时,何武诸人不宜自不量力,而应以保命全身为首要之义。《汉书补注》王先谦引黄震之言日:“班氏说未然也,武、嘉以刚正之资居大臣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贤如杀狐兔耳,何江河一蒉之足云。师丹引经义,开陈婉切,彼董宏何人哉,而以较胜负也,赏罚何足计哉,君子惟论是非耳。”黄震以儒家大义责备班固,所言固是,不知班氏一贯取向,此赞不过从其命定观推衍而来。
《盖宽饶传》赞亦是如此,赞日:“盖宽饶为司臣,正色立于朝,虽诗所谓‘国之司直’无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终其身,斯近古之贤臣矣。”所谓王生之言,是指本传中王生劝诫盖宽饶的一番话,其言日:“君宜夙夜惟思当世之务,奉法宣化,忧劳天下,虽日有益,月有功,犹未足以称职而报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术各有制度。今君不务循职而已,乃欲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拂天子,数进不用难听之语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扬令名全寿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言足以饰君之辞,文足以成君之过,君不惟蘧氏之高踪,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躯,临不测之险,窃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诎。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裁省览。”王生之言强调明哲保身。班固惋惜盖宽饶不曾听从王生之言,以一己之世界观判断盖宽饶行为,倘若盖氏采纳王生之言,明哲保身,世上又安得如盖生之“国之司直”。班氏所言有误。
命定观对《汉书》的影响还表现为班固对各种灾祸征兆的大量描写。如前所述,班氏以为个人前定的性命可以通过各种征兆来认识,因而在史书中记录了不少这样的妖祥,《昌邑哀王传》日:“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无头,其颈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后见熊,左右皆莫见。又大鸟飞集宫中。王知,恶之,辄以问郎中令遂。”又如《霍光传》日:“第中鼠暴多,与人相触,以尾画地。枭数鸣殿前树上。第门自坏。云尚冠里宅中门亦坏。巷端人共见有人居云屋上,彻瓦投地,就视,亡有,大怪之。禹梦车骑声正灌来捕禹,举家忧愁。”班氏作传每多妖祥之言,刺王、胥王与此昌邑王传皆集有此类言语,司马迁作《史记》则无类似记录。
需要辨别的是,这类妖祥灾异之言在班固看来正常得很,并不属于孔子所不语之怪力乱神之列,《汉书·酷吏·尹齐传》日:“所诛灭淮阳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妻亡去,归葬。”王先谦日:“《史记》作‘尸亡去,归葬’,徐广注‘未及敛,尸亦飞去’,《风俗通·怪神篇》说同。《公羊传》‘陈侯鲍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疏亦引此事为证。班氏盖以为诞而易之。”以此而言,则班氏亦不主怪诞之事,其屡记灾祥变异之事,实出于他命定观以征兆推知性命的习惯思维方式,并不以为与怪诞之事同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