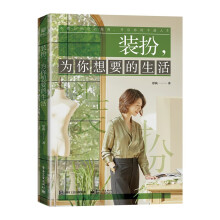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些偶然事件,这就催化产生了一段新故事(只一会儿)——小狐狸精。我尽力追溯事情的源头,说实话,是一双连裤袜改变了我生活的旅程。在我14岁那年,由于与学校的一个修女发生争执,我被女子教会中学开除了。不是那种身体上的冲突,只是因为我穿紧身袜,我们产生了一些口头争执,这导致了我被送到校长办公室,而且后来还被羞耻地送回了家。我再也没有回过那所学校。从小学到高中早期,我都是就读于教会学校。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热爱宗教组织,只是一方面因为私人学校的学费过于昂贵,另一方面我们当地公立学校所呈现的犯罪报告令我的父母心里感到惊恐不安。在12岁时,我被送去位于伍尔维奇的圣母修会学校,那天我穿着擦得锃亮的英国其乐皮鞋和棉质连衣裙,戴着草帽。我的弟弟杰克去了市里的圣玛丽男子高中,穿着我从没见过的一套深色西装,像是要去参加葬礼。我另一个弟弟威尔,才刚开始上小学。新学校里有一些陈旧的、修女式的制度我还是很受用的,整个学校大体上让我感觉很温暖。“我们要团结一心,做到最好”这样的口号着重致力于课外活动(真的是非常有趣的活动),以及短暂的宗教课程。我是辩论队的队长和戏剧小组的成员,记忆中那个小组的口碑还是很好的。我们在家政学的课堂上学习烹饪与缝补,大概大家都想成为全能的家庭妇女。但到最后这门课停开了,不过当时还有小学教师、护士或者秘书学院等别的职业课程可供选择(我不是优等生,所以很有可能是学校鼓励像我这样的学生去选这些课,而不是因为有这些课程)。直到六年级时,夏天的校服都是及膝的涤棉连衣裙,有着“马桶圈”似的领子,颜色是蓝白格子的。领子有着海军蓝的斜纹滚边,校徽别在左胸前,下面写着拉丁语的“VirtussuperOmnia”(大致意思是“百事善为先”)。冬天的时候,这条薄裙子就换成了令人鼻痒的蓝色羊毛罩裙,以及有着另一种丑领子的长袖衬衫,打着领带,下面是蓝色菱纹的连裤袜。这还没有我之前小学发的褐黄色校服糟糕,尽管如此还是很可怕。当我们的校车经过隔壁公立高中时,里面那些邋遢话多的学生就冲着我们喊:“如果小狗会飞的话,那伍尔维奇就是小狗的飞机场!”我对这样丑陋的校服感到非常不满,在接下来的路程里我都会羞耻地放低座位。我的母亲,毫无疑问,她整日沉浸在她那不幸的婚姻和照看三个孩子的劳神疲惫里。如果我告诉她我需要多买几条连袜裤上学用,并明确表示说这次能给我买一双不透明的紧身袜而不是菱纹花型的袜子,她还会无动于衷吗?任何长期穿校服的人都会知道(实际上,设计者也会告诉你),想要把它穿的好看,稍微小小的改动就能改变整体外观与气质。这里一些褶边,那里包边袖口,看起来就是通用款与高级定制剪裁的区别、是穿麻布袋还是穿别致款的不同。为了摆脱备受嘲讽的麻布袋校服,连裤袜是我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展现个性的一步。第一次穿连裤袜去上学的那天,我满心喜悦,心里紧张得七上八下的。我走向公交站台,意识到我今天穿的超前装束,于是很耐心地等待那辆喷着烟的黄栗色公交车出现。到学校时,艾玛(辩论队的第一辩手)看了一眼我的腿,挑了挑左边的眉毛对着我诡异地一笑,在挽我胳膊之前轻轻捏了一下我的袜子。我们走下石阶去开晨会的教室,那里能让我的连裤袜摆脱关注。但并没有太久,当我们离开教室再一次爬上石阶去实验室上第一节课时,我感觉我的肩膀被拍了一下,回头看见一个严肃的修女用她长而尖的鼻子盯着我,她嘴角向下抿着,而且眉头紧皱着,整个表情像是挂了一张反对文书。“我可以请问下,你穿的是裤袜吗?”“哦,这是我的新紧身裤,”我说到,轻微抖动的声音暴露了我的紧张感。“妈妈买给我的,她一定忘记要买有菱纹的了!”“哦,真的吗?”她问道,很显然不相信我说的话。“那好,我就打电话让你妈妈来接你,因为你必须回家换掉它。走!”出乎意料的是,我居然转身走开了。假装没听见她在说什么,并且作为怯懦的抵抗,低声嘀咕骂了一句“婊子”,企图引发艾玛的笑声。但当我说出口时被她听到了。“你说什么?”修女怒喝道。“跟我去见拉姆修女!”她抬起颤抖的右臂,指着不详的校长办公室。这就是我出现在办公室的原因,悲惨地与这个素未谋面的可怕女人面对面坐着,看着她与我母亲通话,毫无疑问,我等待着她们俩给我一顿严厉批评……当母亲得知发生的一切,尽管我坐在几公尺之外,还是听见桌上电话听筒里她难以置信的尖叫声。对于一个打两份工还抚养三个孩子的女人来说,因为一双连袜裤而把我从学校接回家,这件事情似乎很荒谬。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我想应该是拉姆修女输了),我被送去门厅等母亲来,当接线员用迟钝的音调接通我母亲的电话时,我正坐在恶心的棕色布面椅上,暗自悲伤地扯着那上面的脱线。45分钟之后,我被一声不吭的母亲不情愿地接回去了。接下来的几天都在父母亲的争论中度过。我母亲的激烈言辞占了上风,她提议将我送去发廊里工作而不是重回学校,因为,第一,这些修女很荒谬;第二,我看起来也不擅长学校课业。她的理由是,继续读下去是浪费教育机会,现实社会里有我所需要接受的所有教育。我带着悲伤忧愁的表情乞求父亲希望与他进行一次轻松的交谈,但是他拒绝与我说话。我第一次开始渴望下课和午餐休息时间的玩闹,怀念与同学们玩跳房子游戏和手球的时光,梦到跳舞和男生。但是我知道除了接受命运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