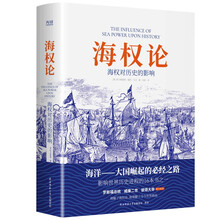在上一节,本书集中讨论了以1945年前后为界,欧洲国际关系进程为什么会由百年冲突状态转轨为进化合作状态?换言之,一个现实主义的冲突环境何以滋生出自由主义的进化合作,难道国际关系之运行也存在着某种类似于生物学变异的政治“突变”吗?透过建构主义的进程分析视角,本书认为,这是一种全球国际关系进程与欧洲国际关系进程互动作用的偶然性结果。在第四章中,本书强调了复合结构的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对于体系进程演化的极端重要性,在这里,历史的发展恰好满足了实现和平所需的两个关键性条件:
其一,体系暴力因历史偶然机遇而获得收束和控制。由于美国的外在干预和内部欧洲共同体的建立,欧洲体系中的暴力使用前所未有地得到合法性控制,虽然没有达到中国历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状态,但现实主义意义上的体系“无政府状态”却日渐被主权国家之上的“共同体状态”所取代,各个主权国之间相互使用武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不仅变得极为困难,而且也越来越不合法。其二,聚合性认同开始形成并日渐增强。随着全球权力结构的变革,在欧洲层面,一种以强调“欧洲团结”与“欧洲联合”为主导特征的区域体系文化正在取代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进而,一种“温特式的”自由聚合性认同开始取代“施米特式的”现实分离性认同。在新的体系观念结构下,即使是共处于同一个狭小的政治地理空间内,他者也已不必然是自我生存意义上的敌人,反而成为可以合作共荣的伙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