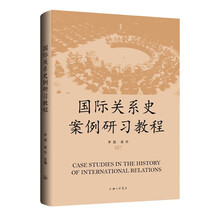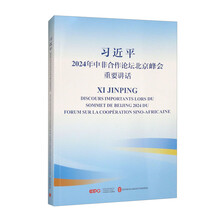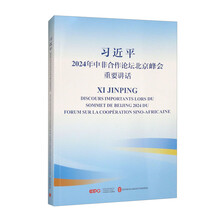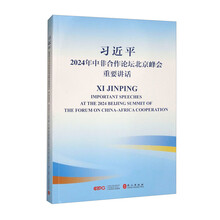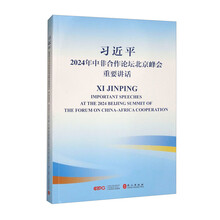洋务派有志遗使出洋,主要是基于对其实用价值的认识。总署大臣在办外交的过程中,发现遣使出洋至少有两点益处:一是了解各国的政俗人情,以减少制定外交政策时的盲目性,即“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二是在外交上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开辟与各国政府直接交涉的途径,“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便可“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
因此,他们把遣使出洋作为办好外交所必须进行的一项改革。1866年,他们作为遣使的试探,曾派总税务司署的文案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然而,在正式遣使的问题上,他们却遇到整个社会的阻力。虽然在1866年令各省督抚筹议赫德、威妥玛“二论”的上谕中写道:“至所论外交各情,如中国遣使分驻各国,亦系应办之事。”表明清廷对于遣使之举已基本首肯,但是,当时的许多官员,对此仍充满疑虑。他们有的认为这会“以柱石重臣弃之绝域,令得挟以为质”;有的甚至担心,“我如派官前往,彼必如论略所云,东西各国代国大臣前来住京,每得入朝秉政之说,而与我使臣以秉政之虚名,即藉口要挟,以求秉中国之大政”。这些担忧尽管均属臆测,但却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表明在风气未开的当时,遣使之举是不受人赞赏的。
中英修约将临,对于清政府固然是一大危机,但同时也是它统一内部意见的一次机会,使它的一些改革措施在贯彻时遇到较少的阻力。遣使出洋就是其中之一。总理衙门早在9、10月间就与赫德在商讨出使的问题,它致各省督抚关于修约的《条说》,则把遣使列入其中,认为它“亦关紧要,未可视为缓图”。
不过,尽管总理衙门已表示了决心,但实际操办起来,却仍颇费踌躇。从表面上看,“使才难觅”是个问题,“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侮,转足贻羞域外,误我事机”。然而更重要的是,中西间的文化隔阂,使得“中外交际,不无为难之处”。总署大臣也残留着天朝至尊的意识。那时,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一直迁延未决,遣使各国若按西方礼仪行事,难免影响国内在这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使维持至尊之体的最后一道屏障不攻自破。因此,当他们找到蒲安臣为使时,似乎发现了回避这一矛盾的出路。这样做,一方面能使他们收遣使出洋的实益,另一方面又可避免中外礼仪方面的纠葛。正是这种如意算盘,使他们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由此可见,在任命蒲安臣为使团首脑的问题上,清政府其实是想维持它那些残存的至尊国体,而不是想以此取媚外国。如果说清政府此举是把它的命运交给一个外国人操纵,那就未免低估了这个有两百余
年统治经验的封建专制王朝。它在派蒲安臣出使的同时,还派了两个中国官员一同出使。总署章京方溶师是出使章程的起草人。他在给文祥的信中指出:“溶师章程中恰专重中朝两使。”即突出两个中国官员的地位,防止蒲安臣大权独揽。这表现在规定志刚、孙家谷二使与蒲安臣地位平等,“皆一体平行”;二者分别颁给关防,“于印用关防须由志、孙两使主持,不使他人干预,亦防其渐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