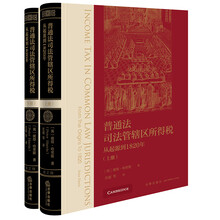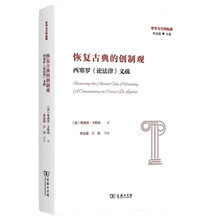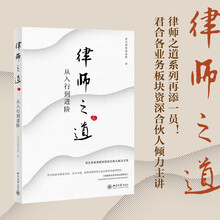法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怪物,存在了数千年也被人研究了同样长的时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能让大部分人普遍接受的准确定义。作为一门学问,它博大精深,一个人穷其毕生精力经过几十年的修炼也只能窥其冰山一角;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却连山野村夫也能在田间地头对它评头品足,说得头头是道。随便翻开一部中国古代的法律典籍,要想理解其精要,哪怕是粗懂其文字,对我这个以中文为母语的法律专业科班生来说都会望而生畏,可最早对这套传承久远的法律体系作出系统判断并影响其政府对华政策的,却是来自西方的这样三种人:传教士、商人和水手。传教士曾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最初的和最为主要的渠道,但这些上帝的仆人对于中国法律的描述却大多以他们个人在中国受到的宠辱为坐标,心情舒畅时妙笔生花,就像我们今天的许多法学家谈到英美法律一样,恨不得先沐浴更衣再开尊口,极尽谄媚之能事;心情郁闷时则笔走偏锋,恶语相加,极尽诋毁贬抑之能事,就像今天美国每年都出台用来恶心人的中国人权报告一样。况且这些人来中国时大多已成年,用业已形成的西方法律价值观来对中国法律进行评价怎么都逃脱不了先人为主之嫌。以逐利为己任的商人和以饮酒寻欢为追求的水手们更是肆无忌惮地对他们平素所不熟知、更没有心情去做理性思考的中华帝国法律妄下判断,赚得盆满钵盈时都觉得是自己太有才了,稍遇挫折便从中国法律制度上去找正当的理由,大骂其“枉屈难堪”。特别是当几个水手或因惹事生非或因运气太差命丧中国法网之后,更让他们对这套他们无以参透其精髓的古老法律制度失去了耐心,萌生了撕破这一法网的冲动。
如果放在几个世纪前,他们的这种冲动甚至掀不起任何风浪。然而进入十九世纪,有三个重要的因素的变化却让这股风潮催生了早已绝迹于欧洲的领事裁判权孽种。首先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大规模的工业化和殖民扩张使英法等欧洲国家实力大增,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可以把它们的军队运往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有人生存的角落,最先进的火炮能够轰塌任何一个古老帝国海岸边破旧的防御工事,新的经济金融模式也可以让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发动战争所需要的资金并用从战争获得的高额利润来回报投资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