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与词语误用
一个概念-比喻在没有足够的、确实的所指对象的情况下就是词语误用。
——佳·C·斯皮瓦克:《在教学机器之外》
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妇女词语误用是本书的重要主题。本章中所介绍的分析和描述性材料,将为后面章节中出现的观点做铺垫。在修订文学哲人关于比喻和词语误用的见解时,我也在寻找译解历史内容的方式。这些内容被遮蔽在史学家日常遇到的各类学派或专有名词中,而我们却怀着无邪的诚意仔细地或者说是“谨慎地”阅读那些文献。1因此,本章有两个主要界定。首先要界定的是:什么是妇女史中的主体?“妇女”,这个今天在中国社会理论中被普遍使用的词语,是1920和1930年代的发明创造,在后面的几章中,我把这两个年代定义为“殖民现代性”时期。因为大多数史学家对时代错置(anachronism)问题很敏感,还因为“女人”(像男人一样)一直是一个范畴术语,不是生物存在的描述或社会文化的能指,因此,在“什么是妇女史的主体”这个问题中所引起关注的,是规范或范畴如何形成和稳定的。时代错置问题在此最为关键。第二个界定紧随社会史的方法问题和关注能指事物的身份而来。目前,在中国研究中比较普通的观点认为,新词是语言学上的符号,而不是像我贯穿于本研究所主张的那样,把论点加入到一个时代的“材料”历史中,其后又加入到妇女自身的命名——即这一命名如何变成了一个历史产物——的问题中。2但是,如果新词已经成为社会规范中的条目,词语误用妇女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有关历史性的词语误用的写作,如何才能避开有关性别主体性的时代错置的设想?
过去的未来(Future Anterior)
用现在或一般过去时态书写的历史,在它们把妇女本质的现代信念投射到过去时,经常主张“将其自身建立在妇女真实的基础上”。3它们声称妇女的真实性或妇女的经验跨越了时间、地点、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关系、认知谱系、意识形态环境,等等。它们对妇女是什么进行了定义(例如:有生育能力的社会人),然后,在证据的基础上(经过挑选的、支持其最初概括总结的证据)重申这一主张。这就产生了想得到的证明结果,即证明妇女的工作、意识形态、身体或欲望在社会上是被复制的。一旦史学家假定“妇女”“在社会中”,相关的主张就变得合情合理了。这就是,在过去的人们那里展示或体现他们自己的现在,以为如果我们以足够的细心去研究他们的社会情境,他们行动的动机就可以被理解。此类历史的作者认为主体描述了过去是因为她身在其中,还认为过去解释了主体也是因为她身在其中。有这样的推测,即那些先于我们的人在历史上行动时,知道他们被定位在人类时期中的什么地方。我认为,这种推测潜在地抑制了不时出自于这种普遍观点的推论。照现在设想的样子,过去、现在和未来既在抽象时期也在历史参与者的意识中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序列和一种观点:妇女是可定义、可认识的范畴:
明末时期(16世纪末、17世纪初)有学识的女性和男性创立了作为分析范畴的“女性写作”;许多优秀的作家和选集的编者,无论女性和男性,都享有“女性作家资格”的特权,并创造了一个明显的女作家意识形态。如果这清楚地规定了我们在研究的初期阶段讨论的参数,那么学者们下一步就要转而追溯这一意识形态的起源,并了解它是怎样与其它文化和社会的环境及要求相互交叉的。为什么明代的作家开始关注“女性写作”并试图保存它?人们是怎样定义17世纪“女人”的,更别说“女作家”了?
着重撰写有关过去未来时(比如本书)的历史并不特别关心妇女是什么,即它不关心妇女以前一直应该是什么,以及已知妇女实际上是什么(例如:社会繁衍的主体)。4它也不关心一旦父权制被废除,作为整体的妇女将会是什么的思考。强调“过去的未来”,是要把注意力从理想的典范或有代表性的妇女本身转移到了书写和思考上,这些书写和思考的重点是译解妇女及其被建议的未来角色。它不太看重普遍主张的内容而更多看重提出主张的政治。潜意识上,这一重点的转移,为调查研究增加了灵活性和实用性,因为它让女性主义学者和支持者能够识别,在即时或特定的时刻有什么可能一直是关注的东西。意识形态可以制约想象的或书写下来的东西,书面表达对环境所具有的真实影响,也都是要关注的重要方面。但本书要强调的是发明创造的行动。它特别感兴趣的,是思想注入到政治事件中并确实完全地构成了一个事件的方式。
历史性的词语误用
最初,我提出黛安娜·伊拉姆对“过去的未来”和历史不确定性的见解是书写历史的一种有用的模式。17到19世纪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历史讨论——对信息内容(描写、政治背景、分析、时期划分、焦点等)及其方法论的设想——引导我辨识了极具吸引力的历史性空白。在下面的部分中,我提出的几种方法,可能有助于解决高彦颐展现的妇女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困境,这或许对转变胜任历史写作的主体观念也有所帮助。性别本身和妇女本身(我称之为历史性的词语误用)都不能够作为一种精确的历史解读的结果出现,也不能把字面词语看作是有关社会规范的存在论或编码陈述。字词使涵义即刻稳定,但历史性的词语误用却缺乏
真实的能指,因而 在多方面显示了其分析的不充分。此部分的任务,是开始思考为什么词语误用的书写历史可以有助于解决高彦颐的双重束缚。依据经验来说,如果妇女只在她们承认自己是妇女时作为一种性别出现,那么,其前提就等于她们既不存在又是殖民的中国女性主义所称的“男人的工具”。
以邓津华和保罗·柔泽尔两个人的观点看,新的中国妇女性别史(它所传达的都是精英们的生活)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具有将其论据依赖于时代错置的女性主体的倾向。邓津华和柔泽尔指出,正确的历史书写,将不再重复对背景——即人们过去用以“区分性别” 的东西——及其假设的依赖。坎康·散贾丽(Kumkum Sangari)与苏德西·韦德(Sudesh Vaid)做了同样的提议,要为性别设立一个思想环境而不是一个社会成就。在他们的阐述中,性别不要求妇女跨越差异去承认共性。更确切地说,这是历史方法的一个基础或方面。他们认为,“女性主义编史把史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反思,抛弃了将妇女框定于某种语境之下的观念,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将性别差异思考为两种形态:既在构建之中,又已经被一整套广泛的社会关系而建构”。
注释
1.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谨慎阅读》(For a Careful Reading),摘自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等主编《女性主义者的争论:一次哲学交流》(Feminist Contention: A Philosophical Ex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127-143)。
2. 有关性别历史和再现辩论的起源参见琼·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的《性别与历史政治》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还可见酒井直树(Naoki Sakai)的《现代性及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问题》(Modernity and Its Critique: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i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7,no. Summer 1988,pp475-504)。
3. 黛安娜·伊拉姆(Diane Elam)在《女性主义和解构》(Feminism and Deconstr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p41)中指出:“与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历史时态不同,用过去未来书写的历史不主张预知女性能做什么和能成为什么;女性的激进潜能并不是与过去决裂的结果,也不会在任何由过去或现在提供的其它保证形式中找到。反之,‘过去的未来’强调基本不确定性,并期待其自行转变。……用过去未来书写的历史是传递给未知接收者的信息,并认为其含义部分将由接收者而定。”
4. 关于“过去的未来”一词的争辩出现在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等主编的《女性主义者的争论:一次哲学交流》(Feminist Contentions: A Philosophical Ex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一书中,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和杜希拉·康内尔(Drucilla Cornell)之间展开。简要地说,康内尔把对“过去的未来”中的历史感悟归功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并认为,历史书写中的女权主义拉康式的时间性显示了理想化的女性气质的潜力,这一潜力超越了现时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它将女性气质贬低成为一个有缺陷的男性气质形式。 康内尔认为琼·斯科特就是这样的史学家。另一方的巴特勒指出,拉康的符号是正常化异性恋特定观念的简单投射。 因此任何在历史书写中对过去未来时态的运用都需要承认这一点,即性别差异“既不比其它社会差异形式更重要,也不在复杂的社会权力映射之外被理解。”(巴特勒:《谨慎阅读》, 第142页);和在同一卷中的, 康内尔:《反思女性主义时代》(Rethinking the Time of Feminism, pp145-156)。我在黛安娜·伊拉姆的《女性主义和解构》概述中见到了“过去的未来”这个概念,它使我解决了一个我时常困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伊拉姆的见解信奉的不是拉康而是克里斯蒂娜·克劳斯比(Christina Crosby)的专著《历史的结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与“妇女问题”》(The Ends of History: Victorians and“The Woman Ques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1);同样,康内尔相信斯科特的《性别与历史政治》。换言之,伊拉姆和康内尔每一个人都瞄准一部历史专论来证明她们的理论观点。伊拉姆、康内尔和巴特勒都在研究“传统”,该传统创立于1970年代末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者和拉康精神分析在有影响的理论杂志m/f上首次爆发的辩论中。争论的焦点是,在女性主义中如何构建妇女以使其成为女性主义妇女史的主体。即时的问题是基本性的:如果女性不仅仅是用语言制造的(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在话语上被构建”),那么什么是她语言以外或外在性的本质?
长达25年的拉康辩论已经形成了理论女性主义,依我看,它们最重要的贡献是对逻辑的贡献。拉康逻辑悖论的破坏性使其难以在简单的自我心理发展逻辑或简单的历史实证论中持续。无论如何,我的确想指出,理论家们还没有领悟到史学家带给书写和思考历史的真正力量。“历史”作为一个略无定形的实体——已和那些研究和书写它的史学家们脱离了开来——出现在许多理论家的论著中。有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我这一观点,那就是在《非殖民化的女性主义》(Feminism in Decolonization;in differences 3, no. 3,fall 1991,pp139-175)中琼·斯科特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之间交流的失败。在该著作中,后者努力尝试过却没有真正达到从历史上解读证据的标准,而前者对斯皮瓦克提供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又过于客气。
5. 伊拉姆的《女性主义和解构》(41)论述了避免现代时代错置的重要性。见克里斯蒂安·德·皮(Christian de Pee):《对后现代中国婚姻的商榷与再商榷:文本的实践VS从文本到实践》(The Negotiation and Renegotiation of Premodern Chinese Marriage: Text as Practice versus Text into Practice,in Positions 9, No.3,Winter 2001)。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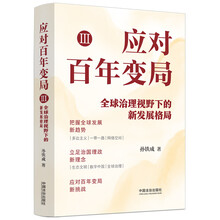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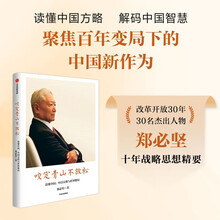



——贺萧(Gail Hershatter),《危险的愉悦:二十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作者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是穿越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激奋人心之旅,涵盖了整个20世纪的理论嬗变。
——罗丽莎(Lisa Rofel),《另类现代性——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的性别化渴望》 作者
汤尼·白露将女性主义思想置于以优生学词语定义人类生活的连续统一体中,展现了中国女性主义并不仅仅是西方思想的遗产,而绝对是现代性的核心及其对有性人的重视。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将引发争议,并最终将成为我们所有人追随的学术榜样。
——温蒂·拉尔森(Wendy Larson),《当代中国妇女与写作》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