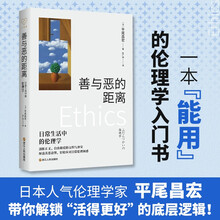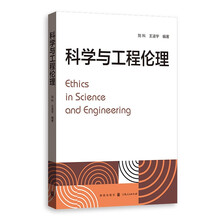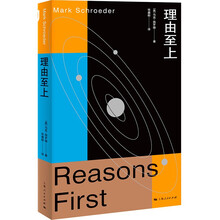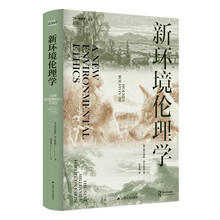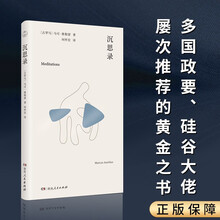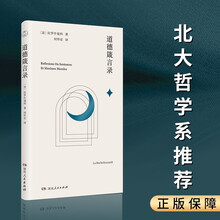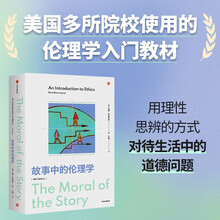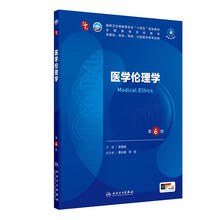第二,“高贵的腐败”的准因果性与目的式辩护不兼容。主张“高贵的腐败”可辩护的主要理由是该行为指向一个善的目的。辩护者所凭借的“善的目的”指行为主体在意志中现实化的行为目标或目的。辩护者所赞同的“高贵的腐败”是指帮助这些目的实现的腐败行为。也就是说善的目标的实现必然要以主体意志介入的破坏行为为中介,那些被破坏的对象本身不是行为主体欲求的目标,但是要实现那些目标,有些东西必然要被破坏、被违反。在警察伪造证据的案例中,伪造证据的目的是为了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但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警察必须违反其职责要求。显然,破坏制度、违背职责并不是该行为的直接目的,但是警察一定要通过破坏制度和违背职责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制造伪证的行为一旦确认,它必然隐含着破坏制度的后果。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了腐败行为是具有因果性的,尽管这种因果性不像“打开冷气,温度就会降低”那样直接;我们也看到腐败行为是具有目的性的,但是这种目的性不足以将腐败行为从不道德行为中甄别出来。谈及善的目的,辩护者怀想的往往是以后果形式呈现出来的好的事态,或者某种假言式意愿。无论是何种情况,腐败的准因果性质决定了目的不能为其提供合理的辩护。
第三,对“高贵的腐败”的辩护不具备道德判断中的优先性。“腐败”隐含着秩序与过程的理念。秩序理念奠基于如下形而上学假定:(1)善与恶的区分是存在的,且存在用以判断善恶的秩序理念;(2)世间的一切要最大限度地被秩序化,且价值内在于秩序系统之中。过程理念以善恶关系为基础,将腐败视为善被剥夺、秩序被瓦解的过程;也是由善趋恶的过程。腐败总是关于过程的言谈,我们从作为善的秩序与关系中去把握这些过程的起点,又从作为恶的表现的异化与错位中去把握这一过程的终点。腐败本身不具有实体性,它栖身于善,更准确地说是依附于作为意义总体的秩序。“高贵的腐败”以“善”之名为腐败辩护时,恰恰误解了“善”的所指。当我们为腐败辩护时,我们必须先确定它所依附的善。只有从善的缺乏和被破坏的秩序之中,我们才能觅得有效辩护的合理性基础。在腐败语境下,对秩序或制度的维护往往优先于对其他诸善的提升。对于伪造证据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的警察来说,伪造证据的行为虽然成就了他自己的私人判断,却破坏了公正客观的司法制度。主张正义的行为诉求并不会改变行为本身不正当的道德性质。所以,即使“高贵的腐败”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辩护,相对与行为正当性而言仍然不具备优先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