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面的现象学——附论“人面桃花”的诗学
夏可君
中国文化是一个讲究面子人情的文化,人的脸面如何呈现,如何体面地端呈出来,这本身就是礼物,给出自己的笑脸还是愁容,这本身就是礼物,如此裸露的礼物。
脸面本身就是礼物,而且是裸露着的礼物,这似乎是某种自然性,某种动物性的余留:人总是通过衣服或者语言化符号的中介来遮盖这种裸露,对于中国人,脸面的裸露似乎是要接受考验的,因为脸面总是会暴露出一个人最为自然的本性,以至于《论语》会说“色难”。
脸面(respect-face),几乎无法遮掩,因此也可能最为需要遮掩或者保护,前者就形成伪装,虚伪的假装;后者则需要爱抚(caress),需要呵护;在二者之间也会形成中国文化特有的“脸谱”,因为中国文化并没有西方戏剧严格意义上的面具观。
中国哲学之前并没有就脸面或者“面子”等进行哲学思考,尤其是没有进行严格的现象学考察,尽管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学上,尤其是面子关系的社会学上,对面子人情及其导致的礼物交换等等有了广泛的讨论,但是依然没有在哲学上展开细致深入的思考,这是哲学的任务。
法国犹太哲学家莱维纳斯(Levinas)却已经对此有严格分析与思考了,从身体现象学走向了面容的现象学或者神学,并且走向了超越面容的踪迹的爱抚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参照。
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中国文化礼物交换的逻辑也同样进入了赝品时代,如何超越这个资本与礼物交换的魔咒的逻辑?这是无所给予,是给出你所无,是给出一个新的裸露的未来,在面容的给出上,有着这种未来的裸露?有着超越交换的新的给予吗?这是诗意的给予,是给出你所无的诗意的礼物!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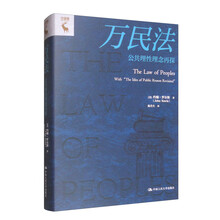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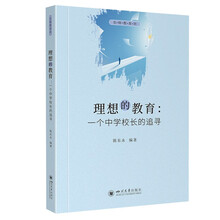


陈晓明:《别了,父亲和长篇小说》
周德伟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一个市场主义者,文化上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前两者间无隔阂,当不奇怪;可怪在于,两干多年前的传统儒家又如何与现代自由主义走到一起。……“成功的自由社会在一甚大的范围内,乃接受传统、尊重传统并导传统于发展之途的社会。”
邵建:《一个儒家自由主义者》
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现了诸多人和动物的对立性差异,这种二元论如此地顽固,以至于从19世纪以来,我们也看到了现代哲学对人和动物二元论的几种摧毁方式:人和动物都囊括在生命的范畴之中从而抹去了它们的实质性差异;人和动物处在相互的生成过程中从而穿越了它们的既定沟壑;人和动物组成了一个不可分的机器装置从而摧毁了它们的功能性分工;人和动物构成了伴侣关系从而拆毁了他们封闭性的主体性界限。
汪民安:《如何想象动物?》
改变大环境,坐等是等不来的,最好的办法是从可以争取的地方去争取,一点一滴做起,努力越多,希望就越大,越多人参与进来,就越可能避免集体悲剧的结果。
刘军宁:《话说民主政治:怎样超越治乱循环?》
在“唱”、“念”、“做”、“打”四项中,梅的唱工戏居多。但梅的歌唱又与程、尚、荀的重心不同。……中年之后,梅的歌唱是着重唱情绪,唱性格,唱笼罩在情绪与性格之上的文化氛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游园惊梦》……
徐城北:《梅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