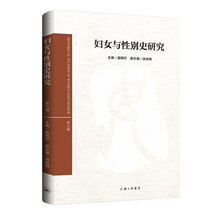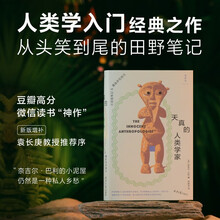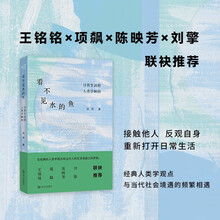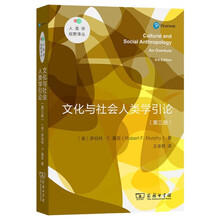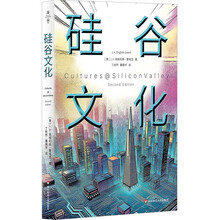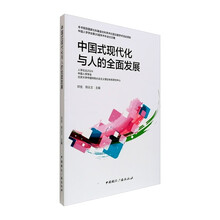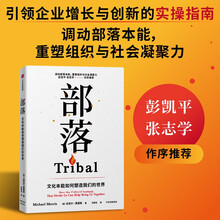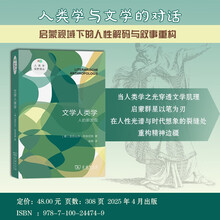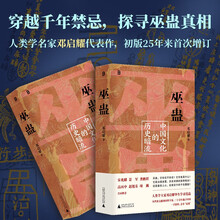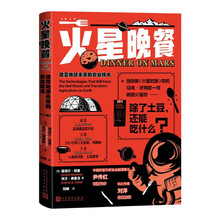总之,《易经》在阐发、推进中国古代“执两用中”或“持中致和”的思维方式方面,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易经》义理并不就是美学,但其内核部分与美学息息相通,那种阴阳和合则上下通畅,天地细组则万物化生的情态景状,那种由各种矛盾事物的谐和如一而形成的鲜活灵动、生机盎然的大干世界,不正是美的理念、美的世界吗?所以,我们以为,《易经》对于中国美学的意义主要有二,第一是以“阴阳两仪”的思想模式,在美学本体论上确立了“执两用中”或“持中致和”的“中和”美范型。第二则是提出了一系列以对耦形态出现的理论范畴,如“象”与“意”、“刚”与“柔”、“动”与“静”、“内”与“外”、“天”与“人”、“文”与“质”,等等。这种对耦形态的范畴系统的形成,与“阴阳两仪”的思想范式是有因果联系的。正是这种民族特色极为鲜明的理论话语,成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2)儒、道两家美学
《易经》的“阴阳两仪”思想范式总体上看还较为宽泛和抽象,缺乏现实具体的社会内涵。这一思想模式还有待于同社会、人生的现实实践相结合,以思考和解决感性具体的审美与艺术问题。于是,这一美学史上的重要使命,便由儒、道两家承担下来了。
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可以看做《易经》中的“阴阳两仪”思想范式在社会伦理和个体生命这两个现实性审美层面上的具体表述、具体展开。儒家主要思考的是如何解决社会伦理与个体情欲之间的矛盾,道家着重关注的是如何消除自然本体与生命本性之间的分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其共同结构都是两两相对的,都是对耦形态的,而儒、道两家所提出的解决各自矛盾性问题的话语策略也同样是“持中致和”或“执两用中”的。
儒家创始人孔子明标“和为贵”(《论语·学而》)说,但孔子所讲的“和”主要是一种“中和”,或者叫“中庸”。他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把“中庸”视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实际也是最高的审美境界(在孔子那里,道德与审美是浑然交融的,兹不赘述)。何谓“中庸”?就是持守中道,不偏不倚,也就是“中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