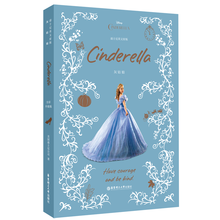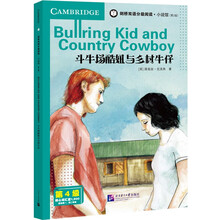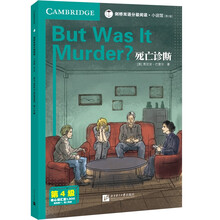经常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规律的鸦片吸食者的。很多熟识我的人也误以为我只是为了人为制造出令人愉快的兴奋才长时间沉溺于此的,并因此不得不承受所有这些苦楚。其实这是对事实的歪曲。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的确是为了鸦片带给我的那种异常快乐的感觉偶尔吸食。但每当我怀着这样的想法吸食鸦片时,为了重新获得那种肉体的愉快感,总是会间隔很长时间才吸一次,这反而能更有效地抵御肉体上的痛楚。我第一次把鸦片当成我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时,并不是为了制造愉悦感,而是为了减轻身体上的极度痛苦。在我二十八岁那年,我感到胃部非常疼痛,难以忍受,实际上在之前十年我刚得上胃病的时候就领教过胃疼有多厉害了。我之所以得上这种顽疾,是学生时代长期忍受饥饿所致,在其后充满希望和幸福的年月里(也就是十八岁到二十四岁之间),胃疼暂时潜伏起来了。再往后的三年,胃疼又开始间歇发作。而现在,在某种不利的情况下,比如精神压抑时,胃疼就会保持猛烈的攻势,除了服用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缓解。青年时代的苦难经历,导致我的胃功能紊乱。这本身讲起来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在这里,我要简单地讲一讲那些伴随这些经历的往事。
我父亲在我七岁左右时去世了,把我委托给四个监护人照顾。我曾经被送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学校,我的古典素养很早就受人瞩目,尤其是我的希腊文知识。十三岁时,我就可以很轻松地书写希腊文。到了十五岁,我的希腊文水平就已经非常出色,我不仅可以用它写出抒情格律诗,还可以流利地用希腊文与人交流。可以亳不夸张地说,在那个年代,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学者能达到如此水平。我之所以掌握了这样的技能,是因为我每天看报纸的时候都要求自己把报纸上的文字即席地用希腊文读出来,这就必须全力搜索我的记忆并且编造词汇,找到各种各样迂回曲折的措词。现代词汇中的概念、意象、事物之间的联系给了我一个措词的指南针,而这样的措词是不可能通过乏味地翻译现代文章而得出的。“那个男孩子,”我的一个老师对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说道,“那个男孩子能够对着一群雅典人慷慨陈词,滔滔不绝,比你我对着一个英国人说的还流畅自如。”这个不吝金玉而对我赞不绝口的人,是一位学者,“一位成熟而优秀的学者”。在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当中,他是让我爱戴和尊重的其中之一。但不幸的是(后来我才得知,让这位杰出的学者义愤填膺的是),我先是被分给一个傻瓜导师,他总是担心我会随时揭穿他的无知,后来又被分给一位可敬的学者导师,他在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里担任校长,这个职位是由牛津大学的某某学院委任的。他倒的确是一位可靠的、修养很好的学者,但是(像这所学院里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人一样)偏于粗俗、笨拙而有失优雅。在我看来,和我最喜欢的那位具有伊顿学者式才华的老师比起来,他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