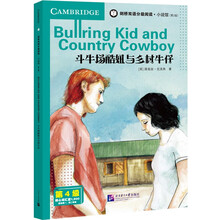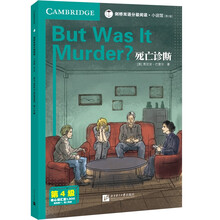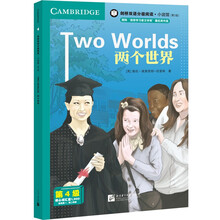去年冬天,我坐在一堆书中间,被书与炉火带来的舒适感与安全感团团包围。也就是说,我背后是一桌摞得高高的书,写字台在我的一边,另一边是几个书架。我一边把脚烤得暖暖的,一边想着我有多爱这些书的作者,多爱这些书——不仅因为它们给我带来了想象的愉悦,还因为它们让我爱上了这些书本身,让我与它们接触时感到快乐。我看看身边的斯宾塞1、忒奥克里托斯2和《一千零一夜》,以及它们上面的意大利诗人;又看看我身后的德莱顿、蒲柏、浪漫小说和薄伽丘;再看着我左手边写字台上的乔叟。我想着,查尔斯·兰姆亲吻一册古旧的对开本其实是多么自然的事,因为我见过他亲吻查普曼译的《荷马史诗》。同时我又想知道,他怎么能做到一直坐在那么简陋的前厅(那里只有几张冷冰冰的桌椅,最多还有几幅镶框的版画),而不是在藏书的后室里摆几把扶手椅(那里起码还有一扇窗户)。如果是我的话,不仅会在两间房里都摆上扶手椅,而且还会多放一两张!“我们可以聊天,先生。”——这是唯一能让人忘记书的话。
我躲进书堆抵御悲伤和坏天气。如果穿廊风刮来,我便四下看看,换个好位置躲避穿廊风;如果愁思挥不去,我便再看一眼我的斯宾塞。我说的“与书接触”,指的是字面意思。我喜欢把头斜靠在书上。虽然我住在南方,但这里离北方很近,能感觉到冬天的气息。每当冬天来临,我就得把一些书从书房搬出来,高高地堆在起居室的壁炉旁,因为只有起居室里有壁炉。因此,我用刚才说过的方法,尽量把自己包围起来。我每天都散步,这种习惯让热那亚人震惊。他们习惯于倚在洒着阳光的墙上,就像苍蝇停在烟囱上一样。但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更好地享受我的英式夜晚。虽然壁炉里烧的不是煤块,而是木柴;但我想象自己身处乡村。我想到了最坏的情况:从我祖国的一端到另一端,不会比从英格兰到意大利更近。
写这篇文章时,我又回到了书房。它像本国所有的书房一样,不是简陋的小间,而是宽敞明亮、装饰得当的大屋子。书房的一侧面朝花园与群山,另一侧面朝峰峦与大海。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我转身背对大海,甚至只要关上一扇朝着峰峦的窗,看见的就只有树了。我左右两边都是书架;前面则是亲切敞开着的书橱。在群书与绿叶贴心的环绕中,我埋头写作。如果说这些都太奢侈、太柔美,那么在所有的奢侈中,写作是最能给人力量的。学术通常来说都是这样。它使人远离运动,虽然对身体不好,但往往能让人的精神力量和使命感成倍增强。文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愤怒,对限制人类心智发展之人更感愤怒。他们像旧时的术士一样,准备给当世的伟人“捣捣乱”,让军人和政客们都吃吃惊。
我不喜欢这间漂亮的大书房。我喜欢雅致的。我喜欢想呼吸便能呼吸、想走动便能走动的房间。我喜欢书房旁边有个大藏书室;而至于书房本身,给我一间四壁几乎都摆满书的舒适小房间就好。它应该只有一扇面朝树林的窗。有些人喜欢没什么书或是根本没有书的书房——比如,爱比克泰德,他的书房里只有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但我想说这些人都是哲学家,而非爱书人,不过我又想起蒙田,他两者皆是。他的书房在一座圆塔里,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四壁全是书。没错,一个人在写作时会忘记自己的书——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说。于我而言,我想我用心灵之眼的余光看着它们,就像是换换脑子——这就如同瀑布或微风一样,算不了什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