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7月24日。
第二天凌晨约四点,虽然天空仍阴云密布,我们还是在店主的陪同下来到湖边,在曦光中,我们在鹿道湖(MooseheadLake)的一块岩石上登上了独木舟。那艘独木舟很小,只容得下三个人,长十八又四分之一英尺,中部宽两英尺六点五英寸,深一英尺。我看它的重量不会超过80磅。这艘独木舟是印第安人近来自己做的,虽然小但很新、很坚固,它是用厚树皮和肋材制成的。我们的行李重约166磅,主要行李按惯例放到了船体中部的最宽处,我们挤进了前后的空当中,脚都伸不开,还有些零散物品塞到了船两头。这样独木舟就装得满满当当的了,活像集市上的篮子。印第安人坐在船尾的横木上,我们都坐在船底板上,后背垫了一块托板以免碰着横木;我们两个人一般有一个与印第安人一起划桨。
我们在早晨的静谧中沿湖东部划着水,很快看到了几只秋沙鸭,印第安人管它们叫Shecorway[阿布纳基语中的秋沙鸭,译者注。],岩岸上还有些斑鹬。我们还看到、听到了潜鸟。短桨有节奏的划水声听起来很带劲,仿佛它们就是我们的鳍,我们终于开始泛舟了。
划过湖边两三英里内的几个岩石小岛之后,我们简短地商量了一下路线,大家同意朝西岸走,因为顺风;否则要是起风了,就不可能到达基内奥山(MountKineo),该山位于湖的最窄处——东部的中间,要是我们向西的话也许能再次经过它。风是横渡湖面的主要障碍,尤其是这么小的独木舟。印第安人有几次说道他不喜欢乘“小独木舟”横渡湖面,但不管怎样,“就像我们说的,这对他没多大区别。”
鹿道湖(MooseheadLake)最宽处有12英里,直线长30英里,但实际要更长。我们沿着湖岸一直划着,不时能听到绿胁绿霸鹟,以及东绿霸鹟和翠鸟的鸣叫。印第安人提醒我们不吃饭他可干不了活儿,于是我们在鹿岛(DeerIsland)的西南主岸停下来吃早饭。我们拿出了食品袋,印第安人用树桩上的白松树皮引燃了一段粗大、泛白的原木来生火,他说要是用做独木舟的桦树皮点铁杉就更好了。我们的餐桌是一大块新扒下来的桦树皮,里面朝上,早餐有硬面包、煎猪肉和很甜的浓咖啡,咖啡里面还没忘加牛奶。
我们吃早餐的功夫,一窝儿未长大的黑河乌,[有几种水禽都叫河乌(dipper),都善于潜水。]有12只,在三四杆[长度名称;约5.029米。译者注。]远的距离内游水,一点儿也不怕人;我们逗留的时候它们一直在附近游荡,现在它们聚成了一团,然后排成一线机警地离开了。
从这里向北望去,看起来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很大的湖湾,我们不知道是应该偏离路线、与我们看到的点保持距离,还是应该找到此处与陆地之间的通道。天雾蒙蒙的,我们已划入过一个小一些的类似湖湾,并从湾底穿了出去,原本我们不得不绕过岛子和湖岸间的沙洲,但那里的水刚好能让独木舟通过,印第安人说,“这很容易搭一个桥,”但现在如果我们继续前行,就可能陷入湖湾。这时,雾散去了一些,露出了北岸的一个缺口。印第安人立刻说,“我看你和我能过去。”
他一般都说“你和我”,而不说“我们”。他从不称呼我们的名字,虽然他对我们姓名的拼法和意思很好奇。我们叫他玻里斯。他非常准确地猜出了我们的年龄,并说自己48岁。
早餐后,我把热过的猪肉倒入了湖中,水面形成了水手们说的“油花”,我看着油花散开,使涌动的水面变得光滑。印第安人也看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就很难划桨了;能把独木舟困住。祖辈是这么说的。”
我们匆忙地装船,把盘子散放在船头,方便随时取用,然后再次启程。我们划着桨,靠西岸很近,岸边的地势渐渐升起了许多,到处都长满了茂密的森林,其中很大比例是硬木阔叶树,点缀在冷杉和云杉之间。
印第安人说我们看到树间垂着的地衣叫“chorchorque”。我们又问他今天早晨听到的几种鸟的名字。常见的是画眉鸟,他模仿了叫声并说那种鸟叫“Adelungquamooktum”;但有时我听到、认识的某些小鸟他也叫不出名,但他却说,“我认识这附近的所有鸟;听声我听不出来,但一看到,我就能认出来。”
我说我应该在他那个印第安人岛上住上一阵子,跟他学他们的语言;并问他能行不?
“好啊,”他答道,“太行了。”
我问得学多长时间。他说一个礼拜。我告诉他在这次旅程中,我会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他,他也应该毫不保留地告诉我,他欣然同意了。
基内奥山(MountKineo)通常都能看到,除了偶尔被前面的岛屿和陆地挡住,如果有云遮住了顶峰,那么湖附近同样高度的山顶都会淹没在云雾中。各种野鸭很常见,它们在我们前面的湖面驰过,像小跑的马一样快。
印第安人问reality(现实)是什么意思,他说曾听我们用过,我费了好大劲才明白是哪个词;他又问interrent,也就是intelligent(有才智的)。我说他几乎发不准字母r的音,都发成l了,有时也把l发成r;如把load读成road,把pickelel读成pickerel,把SoogleIsland读成SugarIsland。他常在单词后加上音节um,如paddlum(划桨),等等。
我们在陆地的某个地方登岸以便活动活动腿脚,顺便观察一下植物;向陆地方向走了几步,我发现了一个余灰未烬的篝火,有人在那里吃了早饭,并留了些细枝晚上用。凭此我知道他刚刚离开,而且一定会回来,凭柴火的量看不是一个人。就算在六英尺之内,你也可能发现不了这些迹象。那里长有长啄榛,七英尺高的芸香,还有紫柳,印第安人说紫柳树皮很好抽,“是白人来这个国家之前印第安人的烟草。”
印第安人在靠岸时总是很小心,怕撞到岩石弄坏独木舟,他会慢慢让独木舟横过来,并叮嘱我们独木舟在岸上时不能上,要等到它完全浮起来,然后才能轻轻地上船,否则会使船开缝,或是把船底踩出洞。
过了鹿岛(DeerIsland),我们看到湖中偏东的地方有一艘来自格林维尔的小轮船。有时我们分辨不出是轮船还是有树的小岛。在这里,整个湖面的风都能吹到我们,真有点儿翻船的危险。就在我盯着一条大鱼跃出水面的湖面出神的时候,我们的独木舟进了一两加仑的水;但我们很快上岸,把独木舟带过沙洲岛(Sand-barIsland)的沙洲,只有几英尺宽,这样节省了很大一段路程。
我们穿过一个很开阔的水湾,那里的浪很大。宽阔湖面的一阵小风也能掀起倾覆独木舟的浪。从岸上望去,一英里范围内的水面可能都很平静,或是如果你看到一些白色的浪花,而且其他水面的浪也差不多,但当划远之后,你会发现浪大得就像在海上,还没等你发觉,一个浪就可能轻轻攀上独木舟的船沿,把水灌到膝盖那么深,就像一只怪物故意用黏液盖住你,然后再将你吞下,或者,水浪会猛烈地拍击独木舟,把它打碎。突然起风时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虽然几分钟之前还是风平浪静;这样除非你能游上岸,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因为独木舟一旦翻了就上不去了。所以说,坐在船底时虽然危险不是迫在眉睫,但一点点水就能造成极大的不便,更不要说食物被湖水打湿了。我们几乎从不以直线方式渡过湖湾,而是沿岸边的曲线前行,这样来风时我们可以更快地登岸。
当风来自船尾方向且不太强时,印第安人会用他的毯子做一面斜杠帆。这样他一天就可以驰过整个湖。
印第安人在一边划水,我们中的一个人在另一边划,这样独木舟能保持稳定,他要换手时会说,“换另一边。”对于我们的疑问,他信誓旦旦地说他自己从未弄翻过独木舟,但别人把他翻到水里过。
想一想我们蛋壳般的独木舟出没在偌大的湖中,在翱翔天际的雄鹰眼里就是一个小黑点
我的同伴边划桨边寻觅鳟鱼的影子,但印第安人警告他大鱼可能把船弄翻,因为这里的鱼有的很大,于是我的同伴同意如果咬钩了,就把钓线立刻交到船尾。
穿过这个湖湾时,基内奥山(MountKineo)就在我们面前两三英里之内黑压压地耸立着,印第安人向我们又讲述了一遍他们的传统,说这座山是古代的一只驼鹿变的——一位强壮的印第安人猎人费尽辛苦,成功猎杀了驼鹿群的王后,它的幼崽也在佩诺布斯科特湾(PenobscotBay)的什么岛上被杀死,他亲眼看到过这座山的形状仍保持着驼鹿斜倚的姿势。他讲了有一阵子,显然对此深信不疑,并问我们猎人怎么能杀死那么大的驼鹿。印第安人在讲述此类故事时都会显得这值得大书特书,只是他没什么好讲的,所以只好用慢吞吞的语调、迂回的策略和沉默来弥补这一不足,希望能增加些感染力。
穿过这段甚不平静的水域后我们再次登岸,然后在湖的最窄处朝东径直出发,很快进入基内奥山(MountKineo)的避风区,然后一直划出去约20英里。现在时间已近中午。
我们计划当天下午和晚上就停留在那里,于是用了半个小时沿岸向北走,寻找适合的露营地。最终,在山侧黑得如地窖般的浓密云杉、冷杉林中走了五六杆远后,我们找到了一个足够干净、平整的地方,砍掉一些树枝就可以躺下来。印第安人用斧子开出一条路,直通湖岸,然后我们运来所有的行李,搭帐篷,整理床铺,以提防恶劣的天气,晚上坏天气确实威胁到了我们。印第安人收集来一大抱冷杉枝条,将其折断,他说给我们当床最好,我想部分原因是这种枝条最大、收集起来最快的缘故吧。雨断断续续下了四五天,所以林子里比平时潮,但他从一棵倾斜、枯死的铁杉下面找到了干树皮,他说他总能找到。
这个中午他满脑子都想着一个法律问题,我让他咨询身为律师的同伴。看起来他最近在买地——我猜有一百英亩——但可能存在法律方面的疑虑,有人宣称已买下那片地今年长的草。他希望弄清楚草属于谁,我同伴告诉他,如果那个人能证明确实在他——玻里斯买地之前买了草,那么不管后者是否知道,前者都拥有该草。对此他只是答道,“怪事!”他说了好几遍,心有不甘地背对着一棵树,仿佛此后的话题已经限定了;他听了关于白人制度的解释之后有所释然,没有继续这一话题,我们也就没再提那个茬儿。
他说他有50英亩的草、马铃薯等,在他家附近、欧德镇(Oldtown)以北的什么地方;他还说雇了很多人干活,锄草什么的;比起印第安人,他更愿意雇白人,因为“他们稳当,知道怎么干。”
吃完饭后我们乘着独木舟沿岸往南返,因为要爬过那些岩石和倒下的大树可不容易,然后我们开始沿悬崖一侧登山。但这时下了一阵急雨,印第安人爬到了自己的独木舟下,而我们因有雨衣遮挡,就继续研究、采集植物。我们送他回露营地避雨,让他晚上用独木舟来接我们。午前曾下过一点雨,而且我们相信阵雨很快就能放晴,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但我们的腿和脚都被灌木彻底湿透了。云朵散去了些许,让我们看到了壮丽的野外景色,随着我们登得越来越高,南北浩瀚一片的大湖以及湖中众多森林覆盖的岛屿映入眼帘,每一边的岸上都满是起伏绵延的森林,茂密得就像黑麦田,连绵不绝得包裹着无名的群山。这真是一个绝美的森林之湖。
向南眺望,天空乌云密布,山峦隐没在云雾中,整个湖都笼罩着阴暗的暴风雨征兆,但湖上六到八英里之处,一道亮蓝色从看不见的天际,穿透飘渺的空气,投射到湖面。此时湖南端也许是晴天。
在这“朦朦雨雾”中,我们又把有着秃树干或树桩的小石岛错当成了带烟囱的轮船,但半小时后它的位置仍未改变,我们才知道看错了。人类的产物与大自然的造物何其相似。驼鹿可能把轮船当成浮岛,直到听到冒烟声或汽笛才会被吓跑。
如果我希望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看到一座山或其他景色,我会选择在很糟糕的天气出发,以便在天气晴朗时赶到那里。此时,我们心情极为惬意,自然是如此清新,令人振奋。泪眼中蕴含的宁静最为沉着。
杰克森在其《缅因州地理报告》中说:“可用作打火石的角石在缅因州的许多地方都能找到。这种石头的世界最大储藏地是鹿道湖(MooseheadLake)上的基内奥山(MountKineo),该山高出湖面七百英尺,看起来整个都是由该种石头构成的。我曾在新英格兰看到过这种角石,印第安人用它做箭簇、战斧、凿子等,那些土著可能就是采自这座山。”
我本人发现过几百个同样材质的箭头。其颜色一般与页岩一样,有白色小点,如果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就都会变成白色。我拾起一小片这样的石头,其边缘很锋利,我把它当成刀,看看好不好用;我用它割一棵白杨,我弯曲着刀刃割了许多刀,倒是割下了一英寸厚;而我的手指也被刀背伤得不轻。
悬崖高五六百英尺,构成了该山南边、东边的半岛,从顶峰我们也许能跳到水中,或是跳到下面看似侏儒的树上,它们长在与陆地相连的狭长地带上。这里很危险,足以挑战神经。
这座山上引起我们注意的植物有在山脚湖畔开满花的山洋莓,崖壁间垂下的美丽蓝铃花,熊果,加拿大蓝莓,野生冬青,圆叶大红门兰,御膳橘,我们登得越高,它们越红,山脚的是绿色,山顶的则是红色,还有一簇簇的矮小岩蕨,现在已结实。探索该山奇观的同时,天也开始晴朗起来,之后我们开始下山。下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印第安人,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喘着气,他一定以为自己快到山顶了。到了独木舟那里,我们发现他在上山时捕了一条三磅左右的湖鳟。
我们返回露营地时,独木舟也被带上岸,倒扣过来,并在上面压了一根原木,以防被风刮走。印第安人砍了些潮湿、腐烂的大块木头,好在晚上闷火。我们煎了那条鳟鱼做晚餐。
我们的帐篷是薄棉布做的,很小,与地面构成了一个三角柱,帐篷有六英尺长,七英尺宽,四英尺高,我们在中间几乎坐不直。搭帐篷需要两个分叉的地桩,一根光滑的梁木,以及十多个用于固定的木楔。这顶帐篷可以抵挡露水、风和一般的雨,这就足够用了。睡觉前我们就斜躺在帐篷里,头旁边放着行李,或是坐在篝火旁,把我们的湿衣服架在篝火前的柱子上烤一晚上。
入夜前我们一边坐着,一边打量着昏暗的树林,这时印第安人听到什么动静,他说是蛇。应我的请求他模仿了那种声响,他发出很低的口哨声——咻——咻——重复了两三次,有点儿像雨蛙的叫声,但没那么响。他说他从未看到过蛇发出这种声音,但到发出响声的地方他发现了蛇。他说这是下雨的征兆。我选择这个地方露营时他就说这儿有蛇。“但它们不会害人的,”我说。
“噢,不,”他回答,“你说得对;对我无所谓。”
他躺在帐篷的右侧,因为,照他说的,他的一个耳朵有点聋,他要把好耳朵露出来。我们躺着时他问我听没听过“印第安人唱歌”。我说没怎么听过,并问他是否能歌一曲。他爽快地同意了,他裹着毯子仰面而卧,开始了低沉,带有鼻音却很悦耳的吟唱,天主教传教士也许曾用他们的语言教过他们的部落。唱完他一句一句地翻译给我们听。他唱的是非常简单的宗教活动或赞美诗,其中的副歌说的是只有一个神统治着所有世界。
他的歌声把我带回了发现美洲的岁月,那时欧洲人第一次遭遇印第安人的简单信仰。其信仰确实有着朴素之美;没有什么黑暗、凶猛的成分,有的只是温和与稚气,而所表达的主要是谦逊和敬畏。
我们栖身的是茂密、潮湿的云杉、冷杉林,除了篝火,就是漆黑一片;晚上醒来时,我听到了身后林中更深处的猫头鹰叫声,还有湖上远处的潜鸟。过了午夜我起来把篝火中分散的木头拢到一块儿,而我的同伴们则睡得正酣,借着快要熄灭的篝火,我看到一个极其规则的椭圆形光环,直径最短处约有五英寸,长处六七英寸,宽度为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英寸。这个光环像篝火一样亮,但不是炭火的红色或猩红色,而是静谧的白色,仿佛萤火虫发出的光芒。我立刻明白这一定是发磷光的木头,我之前经常听说,但从未得见。我略为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指头放到了上面,发现那是一块已死的条纹槭,是印第安人傍晚斜着砍下来的。
我发现光来自紧挨树皮的白木质部分,最终形成了规则的环形,我用刀削去了树皮,砍入树液,树液沿着原木流下,闪闪发光。我惊讶地发现,虽然这块木头可能已从树液开始腐烂,但材质还很硬,明显很完好,我砍下一些三角形的小木片,托在掌中带回了露营地,唤醒了同伴,把木屑给他看。那些木屑在我的掌内熠熠生辉,照亮了我的掌纹,看起来就像烧得白热化的炭火。
我注意到距离篝火四五英尺远的一截已朽的树桩,宽有一英寸,长六英寸,木质松软,也散发着同样的光芒。
我没有去判定我们的篝火是否与这有关,但前一天的雨水和长期的潮湿天气肯定有关系。
我对这一现象极感兴趣。光芒的图案若是文字或人脸就更令人震惊了。我没想过能在漆黑的荒野发现这样的荧光。
第二天印第安人告诉我他们给这种荧光起的名——artoosoqu'——在我对鬼火的探询之下,他说“他们的人”有时能看到飘荡在各种高度的磷火,甚至有树那么高,还能发出声音。我准备好好听一听“他们的人”所看过的最惊人、最超出想象的现象,不管是什么季节和时段,他们都经常出没在白人罕有涉足的地方。大自然一定向他们展现了数不清的秘密,而我们却知之甚少。
我对以前没看到过这一现象不感到遗憾,因为现在的情况更有利。此行我原本就抱着探奇的心思,而荧光现象正合我意,使我随时准备看到更多奇观。我先抛开科学不管,完全沉浸在发现荧光的喜悦中,仿佛它一直以来就是我的同类。科学解释在此处是不合适的。科学是为白天准备的,要是听科学的话,我就会睡去,而不会起身一探究竟;忽略科学正是我提升的机会,使我成为更坚定的信徒。我相信森林并不是无人居住的,而是时时充满了坦诚的精灵,就像我一样——那里绝不是化学即能解释一切的空室,而是有生灵居住的住所。这也表明,相同的体验总是催生相同的信仰或宗教。印第安人得到了一个发现,白人得到了另一个。关于我们的印第安人,我还有很多需要了解,但与传教士无关。我不太确定的是,我之所以要向印第安人教授我们的宗教,是不是因为他承诺教给我他的宗教。很久之前我就听说过不相关的事情;现在终于遇到了腐烂木头发出的荧光,对此我很欣慰。
我把那些小木片收了起来,在第二天晚上又把它们弄湿,但它们却不发光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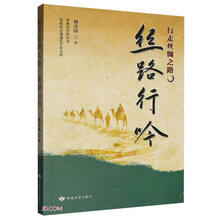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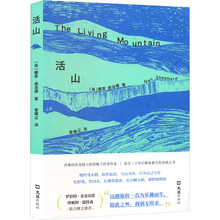



——梭罗
在尘土最肆意飞扬的路上,也有对最风尘仆仆的旅人的慰藉——他时而爬上高峰,时而走入幽谷,他的双脚勾勒出的路径便是人类生活的最完美的象征。
——爱默生
梭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歌颂自然的作家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其魅力与日俱增。他是一个细心而精准的观察者,身处田野和林间时比在村镇更为得心应手,而且他能用新颖的笔调将自己的印象娓娓道来。他的想象力敏锐而灵活,而且与其渊博的常识相得益彰。其叙述充满真挚,摒弃了偏见和浪漫的夸张。
——克利夫顿·约翰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