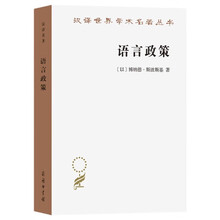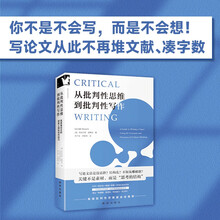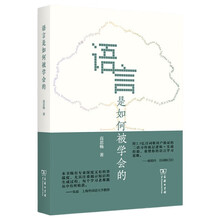巧妙之处在于能精确地标明音节始于何处与止于何处。卢德(Roudet)先生教导我们音节区分可按我们的观点呈现出三个方面。他说:"我们每一次由一个音节过渡到另一个音节都有一个同时影响到呼气调度、发音动作和听觉感受的突然变异。"这个三重变异使我们有可能在若干情况下确定音节的界限;在其他许多情况下,这种区分却是任意的。要想确定这种区分就像想确定两个高山间的谷底确实在什么地方一样都是非常幼稚的。给语音词下定义差不多也是一样任意的,因为往往有些音节,甚至有些音节的组合,我们不知道应该分成独立的词呢,还是把它们归附于相邻的词。有些区分得比较清楚,有些却不大清楚,各随语言而有所不同。重音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我们在上面说过,气息从气管流出后不是始终如一的。空气的消耗不是连绵不绝的。因为调节声管步伐的筋肉有时使它的动作急速起来,有时缓慢下去,因此有些加速,有些激进,有些减低速度,有些休止,拍子数量的多少各随语言和说话者而不同。换句话说,言语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带有强弱拍子的韵律原则。正如我们把一个音乐句子分成拍子而不管它的旋律一样,我们在任何句子里都可以认出一定数目的区分,而不管意义;这些区分当然不像在音乐里那样有规则,而且数值更易起变化,但也一样要决定于强拍子的周期性的循环。语言里是既有高峰,又有洼地的。这些高峰时常有一种心理价值。人们有时认为产生音强和音高的筋肉活动决定于心理的原因。重音似乎是在语音尸骸内部吹进了生命。依照一种借自古代语法学家的隐喻,重音就是词的"灵魂";无论是声调或重读都会使词具有它的性质和个性。但是重音不足以确定词。首先,它只很不完备地标出了词的界限。毫无疑问,在某些语言里,重音的位置决定于词末;在另一些语言里,重音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或词末前的音节;又在另一些语言里,词首念重音。但可能性并不止于此;有些语言的可变的重音毫无词末的表示。此外,有时几个词的组合只有一个重音,或者,相反,一个词就有两个重音。印欧语,比如希腊语或梵语所证明的,有所谓前接重音,没有独立性的小词依附于前一个词。在我们带有重读的语言里,某些词组只用一次发音发出,只有音组的一个音节上带有附加的气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梵语里,有些词就带有两个重音,而且在带有重读的语言里,往往除主要重音之外还有一个次重音。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