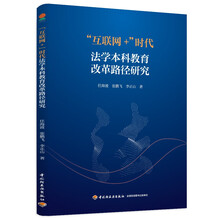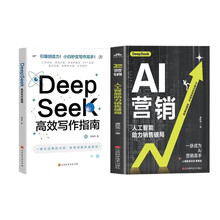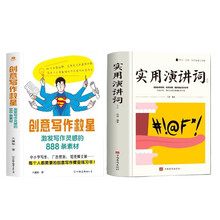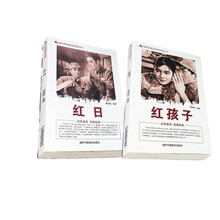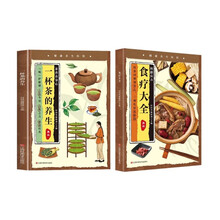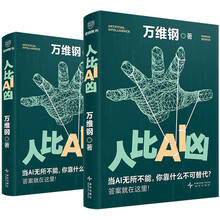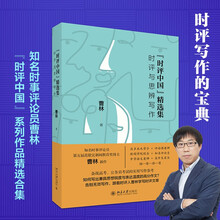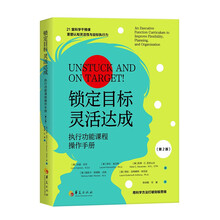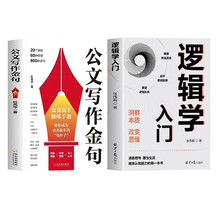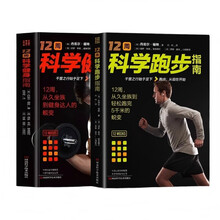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经济的蓬勃发展、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来华学习,来华留学生教育呈现持续快速增长势头,留学生数量屡创新高。同时,也归功于中国近年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的努力,中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纯粹留学生输出国逐步转变为留学生的输入国。据中国教育部消息,2010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847万人《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双增长》,《中国新闻网》2011年3月3日,引自:http://wwwchinanewscom/lxsh/2011/0303/2880033shtml。,而同年各国来华留学生总数达265万人,两者基本上已趋平衡。近年来,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美国,也在其政府、企业界和教育界的鼓励和支持下,掀起了一股迅猛的留学潮,出国留学的人数有了显著的增长,而中国是美国留学生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成为超过德国的第5大留学目的国(前4位依次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数据整理,1998年2010年期间,各国来华留学生总数增长62倍,到2010年达265,090人;而从1995~2009年的14年期间,美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长134倍,2009年已达18,650人,而且在2008年就超越日本,成为来华留学生的第二生源国,仅次于韩国。
虽然整体上中国在留学生教育的进出规模上已趋平衡,但是,在国别结构、类别结构与层次结构上还是不平衡的。如像与美国这样的特定国家,中国的逆差就相当突出。例如,20092010学年中国前往美国留学的学生人数高达127,628人,而美国2009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仅18,650人,前者是后者的68倍。此外,中国前往美国留学的数字都是攻读各级学位的正规学生,而美国来华留学攻读学位的正规学生只有约8%。令人吃惊的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中均未将其列入正规留学生行列的美国来华非学历留学生和被美国政府单独列为语言进修性质的来华留学生的比重竟然都高达92%以上!
这种情况与中美两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力、两国相互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的规模和广度、以及相对于快速增长的美国来华留学生的规模,是极其不相称的。如果说近年来中美两国的总体贸易额中中国一直是顺差,而在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相对于中国学生赴美国留学绝大部分就读专业课程、力争拿学位的情况,美国来华留学生的现状使美方赢取了巨大的顺差。这种情况如继续下去,对美国学生和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将大为不利。
笔者任职的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SAsianCulturalAcademy)长期致力于中美两国文化、科学与教育的交流。早在2006年,笔者与同事即在从事中美交流的实践活动中对上述难题深感困惑和焦虑,竭力希望为改变这种不平衡状况作些实质性的贡献。经与中美两国学者、实施留学生教育的高等院校及政府主管部门的广泛调研与咨询,笔者与美国亚洲文化学院的同事归纳出影响美国学生来华留学的三个最大的障碍:语言问题、中国大学的教学质量问题、留学费用问题。我们随之对这三个障碍分别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语言问题这个障碍是暂时的,在美国学生自身的努力、中美双方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共同支持和帮助下,这个障碍将会逐渐消除。事实上,我们后续的实证调研中也证实了我们最初的判断。对于中国大学的教学质量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棘手。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大学对美国留学生有无吸引力的关键。从目前美国来华留学生在类别结构与层次结构上极为突出的不平衡问题就相当程度上凸显出中国大学的教学质量问题。由于中国大学存在的教学质量问题,也一定程度上连带影响了美国大学对中国大学的学分互认问题,这也更减弱了美国学生来华挣学分和拿学位长期留学的动力。如要分析原因,问题主要出在中国方面,我与我的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同事是无能为力。要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大学只有奋发进取,发愤改革,尽快建立与时代相适合的现代大学制度,早日清除这一障碍。
对于美国学生来华留学的费用问题,从目前来看,这个问题似乎是美国学生来中国留学的最主要障碍,也是笔者与同事最可能有所作为的领域。在中国民众的想象中,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学生应该不存在因经济问题而无法出国留学的问题。遗憾的是,美国的现实却恰恰相反。美国法律规定:义务教育到高中为止,但上大学的费用则全部由学生及其家庭来承担。近年大学学费的迅猛上涨,更使一般家庭的压力增大。由于国情和观念的不同,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提前消费,所以家里甚少储蓄,大学学费又是税后支出,所以很少美国人能够负担得起学费,更难于负担出国留学的费用。但是,美国高等教育法又规定,只要学生被大学录取,美国联邦教育部有以补助和贷款等方式资助其上学的义务。但前提是学生必须进入经联邦教育部授权和认可的认证机构认证合格的大学,以确保学生获取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进入这些大学的学生就有资格申请联邦政府的各项助学金和奖学金。而这一政策也同样适用于在美国联邦教育部认证合格的外国大学中就学的美国学生。
由于我们美国亚洲文化学院的许多同事均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多年、深谙美国法律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这种特殊的背景使我们既能跳出教育系统观察教育问题,也可以摈弃传统的由留学生接受国政府提供更多资助的思维定势,从而在上述美国政府的法律框架和现有政策内探寻到一条利用美国政府的经费招收更多美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新途径。当时,我们部分同事专门拜访了美国联邦教育部负责外国大学认证资格的官员,就此问题与他们进行了咨询和探讨,并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然而,在我们决定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时,我们碰到了项目经费问题。因为该研究对象是以中国为主,且研究成果主要是中国方面受益,故难以在美国方面申请项目资助。
正巧笔者于2007年9月被上海财经大学作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获聘为该校高等研究院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开始回国全职工作,这就使笔者有可能在中国申请科研经费用以资助这项研究。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笔者将课题的总体研究框架进行了重新设计,将原先纯粹是对如何利用美国政府的经费招收更多美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新途径的研究与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发展的大局联系起来,将课题的题目正式确定为《从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角度探索一条更有效吸引美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新途径》,具体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即:中国大学如何利用美国政府的经费招收更多美国留学生以及该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教育等国家利益的影响。
尽管该项研究的价值毋庸置疑,然而课题申请的事宜一开始却很不顺利,几经波折。国内有关项目要么规定申请者不得超过50周岁,要么规定持国外护照者不能申请,这些限制性政策导致笔者在回国后的最初两年期间被排挤在申请国内科研经费的资格之外。直至2009年9月,在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关心下,笔者才获得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为归国人员设立的《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的部分资助,得以启动该项研究,开始在中美两国进行文献资料的前期收集工作。值得庆幸的是,随后不久,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主要领导的关注和推荐下,笔者又于2009年年底(12月)获得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设立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立项资助。至此,作为该项研究的物资基础和政策支持得到了基本保障。笔者据此组建了由部分国内外学者和研究生参加的课题组,并在前一阶段初步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决定在中美两国进行一定规模的实证性调查研究,以便获得第一手数据和资料。鉴此,针对不同对象,我们设计了三套问卷:第一套问卷是针对目前正在美国大学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英文版);第二套问卷是针对目前正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英文版);第三套问卷是针对中国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处、部)的领导(中文版)(问卷具体内容可参见报告后面的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分阶段对上述三类群体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事有凑巧,在研究工作进行了一学期后,笔者于2010年暑假后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入北京师范大学,获聘为该校“985”工程特聘研究员。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批准,将项目管理单位予以变更,笔者也顺理成章地将该研究项目带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以来,笔者特别对北京师范大学为本课题顺利进行和成功完成所提供的各种物资便利和学术条件表示由衷的感谢。在笔者于2010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后,第一,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美国有关法律和政策的文本,通过整理和分析,论证出中国大学申请美国联邦教育部有关外国大学申请资质的法律依据、规定、要求、程序以及可行性与意义,从而在传统的思维和做法外探寻到一条利用美国政府的经费招收更多美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新途径。
第二,组织人员在中美两地同时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全美200多所大学中目前正在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921份;对中国100多所大学中目前正在留学的美国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04份;对中国25所“985”大学和“211”大学负责留学生教育的国际交流学院(处、部)的领导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3份。对回收的调研结果进行了全面和详细的梳理、统计和分析,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据此得出了客观的结论。
第三,借鉴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各学科领域产生的大量前沿观念、案例、文献等研究成果,结合知识经济时代与全球化的时空背景,对实施该政策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和教育等领域国家利益的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理性分析,从中分别得出了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结论。
第四,为使我们的研究尽可能严谨与周全,笔者专门前往香港,对目前两岸四地中仅有的两所已成功申请到美国联邦教育部资证的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进行了实地考察和交流,详细了解了他们申请的动机、目的、过程及项目运作程序,从侧面间接论证和加强了我们研究结果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第五,由于自2010年7月1日起,美国政府将面向在国外大学学习的美国学生申请的助学贷款名称“联邦家庭教育贷款”(FederalFamilyEducationLoan,简称FFEL)项目改名为“威廉D福特联邦直接贷款”(WilliamDFordFederalDirectLoan,简称DirectLoan)项目,相应的一些具体申请规定、要求和程序也作了些微的变动。为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最准确的信息,笔者利用假期专门前往美国联邦教育部,与有关负责官员进行了当面沟通和咨询,及时获取了第一手资料。
第六,由于中国政府对各国来华留学生的定义、标准以及统计的口径与方法有不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统一的规定,其结果是两方面公布的数据有相当大的差异。笔者在处理数据过程中既感到困惑,也颇费脑筋。为寻求适当和权威的参照系,笔者力争尽可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靠拢。根据国际标准,笔者将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和调整,这既是为了建立科学、真实、客观并与国际标准相兼容的数据库的尝试,也是为本课题的深入进行建立起了自己的研究框架。
第七,鉴于本课题兼具宏观政策研究和微观实际应用的双重属性,其应用价值将主要体现在研究成果能够尽快转化为政府决策上和直接指导中国各大学在实践运作方面的活动,笔者将本课题的研究和感受通过报告后面的建议与践行逐一呈现给大家,期望对完善美国和所有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工作中有所参考,同时,也期望能促使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有一个实质性的变化。
第八,笔者认为本课题要探索一条吸引美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新途径的尝试达到了理想的结果:
A既在法理上符合中、美两国的有关法律;
B在政策上也与中、美两国政府的目的完全合拍;
C在实践层面上更是反映了广大美国学生的真实需求;
D剩下的只是研究如何实施的问题。
鉴此,我们认为我们的探索和努力是有效的,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应该说,我们为吸引更多美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找到了一个多赢的突破口。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政策上作适当的调整,每年至少可为国家增加几十亿至上百亿的经济效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