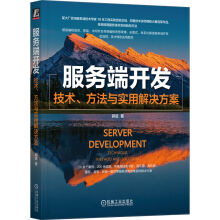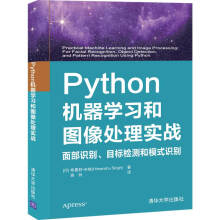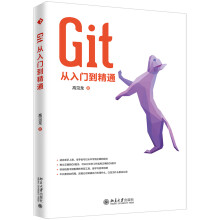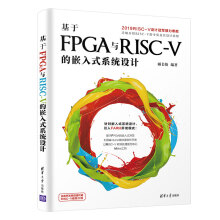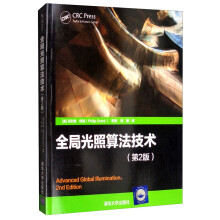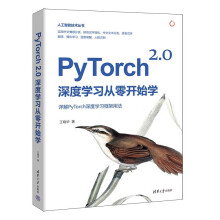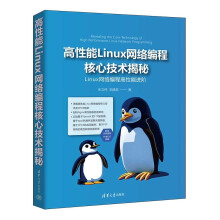但在中国文化里面,理性没有获得这种本体的地位,相反倒是人间的喜怒哀乐等情欲的东西,在《中庸》看来这才是世界之大本。正因为有这种说法,所以梁漱溟先生非常乐观,认为西方近现代才出现了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等以意志、直觉、本能为世界本体的哲学,所以中国文化将来能够领导世界新潮流。这个话题我们暂且不表,我们还是来看中国的理性到底是一种什么理性。中国的理性不是一种将感性鲜活的完满形象切碎的科学分析理性,也不是一种脱离了感性而在超越的思辨王国里翱翔的理性,而是一种以实用价值为导向的伦理理性,就是说人表现喜怒哀乐的时候,需要有一种理性来控制一下,应该以道制欲,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从而调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是这么一种具有交往性质的伦理理性或关系理性。而西方的科学理性与思辨理性,它的好处是使西方的科学非常发达,但坏处是导致了一种工具理性,以至于到了后来,人也变成了工具,现代主义就表现了这方面的很多异化的东西;另一个方面,脱离了感性世界而在超越体验的王国里头翱翔的理性,实际上跟宗教也可以握手言欢。在基督教文化中,理性、灵魂与上帝是一伙的,而感性、肉体与魔鬼又是一伙的,这样的两分恰好使理性和上帝可以握手言欢。而在中国,因为理性永远越不出这种感性之外,所以它就推导不出一个上帝。审美是要诉诸感性的,而中国的理性永远不脱离感性,所以它本身仍然具有一种审美特征。
我们以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为例来分析。笛卡儿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而在“我思”的时候,我和对象之间有一个界限,就是说自然、社会等都是“我思”的对象,我要对它们进行认知和支配。其实整个西方文化都是把主体的我与外在的世界划了一个界限,把对象作为一种科学分析的客体加以观照。于是声称“自由哲学”的萨特,就得出了别人就是威胁我的地狱的结论,因为其他人总是作为我的客体而存在,而我也同样作为他人的客体而存在。而在中国,“我思”和“我思之物”之间就没有这么截然的鸿沟,我在社会当中,与人和谐相处,自然和我是非常友好的,我看花,我到花中去,花看我,花到我中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天人感应,物我合一,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种浑然一体,就像是我前面说过的和合的精神,这更接近一种艺术精神,而那种分析的精神更接近一种科学精神。
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在概念上也能表现出来。中国文化的一些概念都是靠悟性和直觉来领会的,是不能进行分析的,一分析就失去了原来的意思。像“天”这个概念,中国的“天”有它自然的意义,也有主宰的意义,而这两个意义是完全合而为一的,若你翻译成西洋文字的话,就不好翻译。中国的“心”也有这样的特点,“我心想”的“心”就不仅仅是一个肉体的心,还是具有智性的心。可是,这个智性的心又不脱离感性肉体的心,正如叶维廉所说,你翻译成heart,好像太肉体化了,你翻译成mind,好像又太智性化了。但是西方的概念总是要把这两者分开,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概念都是一些综合的概念。所以,中西审美的与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概念的翻译上是首先遇到的问题。在座听讲的好多同学是英语系的学生,将来要是从事翻译的话,那么在翻译的时候肯定会感到中西文化确实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表现为基本概念和词汇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导致在翻译上很难把握。
最难把握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西方非常精确的科学论文翻译成中文,你会明显感到我们的概念不够用,尤其是有时候西方文章中出现的大概一页不断句的情况,我们总感到我们国家的文字好像是不大够用,好在现在使用的白话文已经好多了,要是用文言文,那结果可想而知。中国文化主要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如果让大家用文言文翻译西方那些非常精确的科学论文,是比较难的,因为中国的概念本身就有一个特点,即不是很精确,它是靠着悟性而形成的概念。另一个方面,就是把中国的诗歌、诗学中比较灵动的东西翻译成西方文字,这个也非常麻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