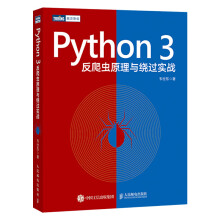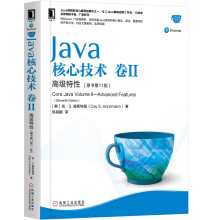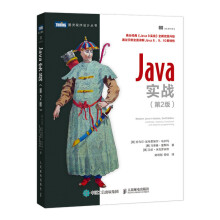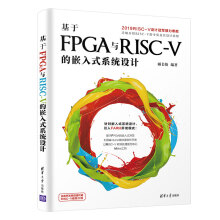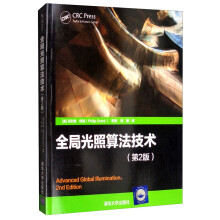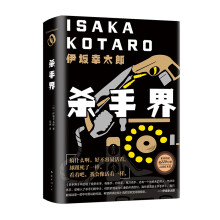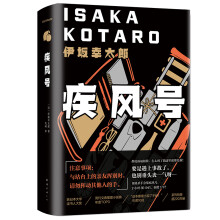第一章 将军令
打狗港像一朵张开巨蕊的花瓣,把铁轨和火车次第吞进深海。泛滥着腥味的洋流旋即重归平静,一如既往的幽暗、冷漠、心事重重。这些生锈的机车,瘢痕累累的铁轨,都来自海峡彼岸。从上海到高雄,千里迢迢的跨海之路,持续数年的外交风波、权力倾轧,终于尘埃落定。只不过,旅程的终点是沉没,而不是重生。
这是可以预期的结局。
风波起自光绪二年(18 76 年),英国怡和洋行强行修建的淞沪铁路通车,在上海引起轰动。铁轨两边的中国民众“立如堵墙”,但他们最初的好奇心很快就被恐惧与愤怒淹没。南洋大臣沈葆桢和上海道台冯光认为此举侵犯了中国主权,冯光甚至威胁英国人,如果火车继续开下去,将不惜卧轨自杀。
1
不久,冯光的预言就兑现了。一名中国士兵被飞驰的火车轧死,这起命案很快升级为外交事件。远在直隶的李鸿章被迫介入。
谈判桌上,两国外交官还在进行着漫无边际的交涉,危机已经伴随着谣言,疾速升温、失控。
停开的淞沪铁路边,开始不断出现一些形迹诡秘的中国人,他们频繁地沿着铁轨游走,压低了帽檐,目光机敏却又变幻莫测。后来,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这些便衣的士兵离开后,铁路两侧就陆续驻扎了大批中国驻军。
租界里的传言则更加悚动,英国侨民们渐渐相信,很快就会有中国人前来寻衅闹事,并可能烧毁洋行。
事实上,感受到压力的不仅是西方的侨民。在租界之外,不安的情绪同样在大肆蔓延,据说有两艘英国兵船已从大连港起航,正星夜兼程赶赴上海。
一场因铁路事故而起的战争,似乎将一触即发。
然而,李鸿章知道,帝国已经不堪一战。
谈判马上加速进行,中国决定出资2 8 . 5万两白银,将淞沪铁路购回自办。
李鸿章所希望的,不仅是化解这场外交风波,他更试图妥善接管并经营这条铁路,将其经验向全国推广。
不料,沈葆桢已经率先下令,将铁路全部拆毁。无论李鸿章和远在欧洲的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怎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沈葆桢仍决定一意孤行。
问题在于,无论是沈葆桢还是冯光,其实都不算是守旧的大臣,甚至,他们还是洋务派的中坚力量。马尾造船厂和福州船政学堂,都是在沈葆桢的主持下兴办起来的,而冯光则担任过江南制造局总办。
他们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一向是开明的,不料,这次的举动却异常的武断强硬。是时代变了,还是他们变了?
沈葆桢的自陈道出了其中的端倪--“铁路一事,虽为时势所必趋,然断不使后之人谓中国之有此,乃由江督沈葆桢而起。”他并非不理解铁路的重要性,他也深知兴建铁路是大势所趋,但他不愿在这个保守的帝国里背负激进的恶名。沈葆桢的顾虑,正是困缚这一代人的精神枷锁。
此外,令沈葆桢耿耿于怀的,是李鸿章过于积极地介入此事。尽管这件事属于外交范畴,也在李鸿章的职权范围之内,但它毕竟发生在沈葆桢的辖区。北洋大臣干预南洋之事,有越权之嫌,这让沈葆桢难以接受。
李鸿章、郭嵩焘与沈葆桢、冯光,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只不过,对声名的计较、对权力的重视,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绑架了理性的判断,由此引发的,则是对现代化的仇恨。
沉入海底的淞沪铁路,就像一则魔咒,不断地警告着后来者,并暗示着帝国复兴的艰难时局。连位居西化前沿的上海都如此保守、偏激,其他城市更是可想而知。
淞沪铁路拆除后,丁日昌要求把材料运到台湾,以助建造台湾铁路。但是此后,由于筹款无方,台湾铁路计划最终不了了之,这些远道而来的铁轨和机车,也只能沦为废物。这迟来的结局又一次激起李鸿章的愤恨,他写信给郭嵩焘抱怨说:“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鄙论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世重科目时文小楷即其根本,来示万事皆无其本,即倾国考求西法,亦无裨益,洵破的之论。……幼丹(沈葆桢)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
事实上,“徒邀取时俗称誉”的事情,李鸿章在十多年以前也做过。18 6 5 年,同样是在上海,当时的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为了通商便利,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提出,要在上海到吴淞之间设置电报线。
李鸿章不便明令拒绝,却暗中授意上海县令,鼓动乡民把英商刚刚树立起来的电线杆连夜拔除。只不过,世易时移,现在的李鸿章却主动在总督衙门和天津机器局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他还踌躇满志地试图继续兴办铁路,继续打造西式舰队。他宣称:“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来,国家此刻凋敝的时局,未尝不是一个痛定思痛的好机会。李鸿章的强国梦想,自然也掺杂着公德与私心,但是,今日的李鸿章,毕竟已不是昨日的吴下阿蒙。他所看到的世界,已经比他的同代人更远,也更加深入。
曾国藩临终前总结洋务运动的实绩时,将李鸿章、左宗棠与自己并列:“窃思铁厂之开,创于少荃(李鸿章);轮船之造,始于季皋(左宗棠);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尽管曾国藩半生致力于洋务,他却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衷,所谓“经世之道不出故纸之中”。
他始终相信,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能在中国漫长而神圣的传统中找到答案。
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另一位国学大师王运的理解则更富戏剧性。同治八年(18 6 9 年),在点校《汉书》时,王运意外地发现了火车的起源,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点《汉书》半卷。梁孝王欲得容车之道,自梁属长乐宫,以朝太后,此英吉利火轮车道始见于史传者也。”
王运甚至认为,《圣经》中引领众人出埃及的摩西,其实是西方人对“墨子”的误读。王运论证说,墨子当年离开中国,一路向西而去,他的名字被西方人读成了“摩西”,而摩西手中的十字架,其实是墨子随身携带的矩尺。
王运所做的这些牵强附会的臆想,代表了中国的精英阶层对现代化的误解,以及对传统文化偏执的狂热;而在民间,这种情绪则更加复杂。直到1910 年,依然有人相信“修筑铁路,必须多数人灵魂镇压,铁轨始得安稳”。
人们甚至认定,朝廷调查户口,其实也别有用心,就是为了把这些写有民众姓名的调查册放进铁轨枕木中,用百姓的灵魂来维持铁轨的稳定。于是,人们不仅对铁路深怀恐惧,甚至满腹仇恨。
流言总是比真相走得更快更远,盛世末世都不例外。一句谣言就足以摧枯拉朽,让帝国长达数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这样一直在反复的类比与猜度、傲慢与偏见之间徘徊,这种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的形态。帝国晚期的改革往往执泥于器物的层面,而无力也无意深入城市内部。城市变革往往浅尝辄止,社会结构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自我调节,城市的真正蜕变也就无从实现。
所以,尽管在晚清被洋务运动和新政青睐过的城市有安庆、金陵、天津、上海、马尾、开平、旅顺、威海……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有天津成为几乎唯一残留下来的活化石。正如史华慈(B e n j a m i n I s a d o r e S c h w a r t z)总结的那样,洋务派的态度其实只是“抽象地赞赏西方”,城市因此也根本来不及发育完善。现代化要在中国生根,需要面对重重的困难-- 国家的沉沦,纵横捭阖的权力斗争,以及文化的傲慢与精神的自卑··它们将这个国家一次次逼入险境,也将中国人的城市梦想一再推向边缘。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这样在起始阶就自相矛盾,并且危机四伏。天津的侥幸胜利,并不能解开帝国的心结,更无法疗救现实的沉疴。
……
展开